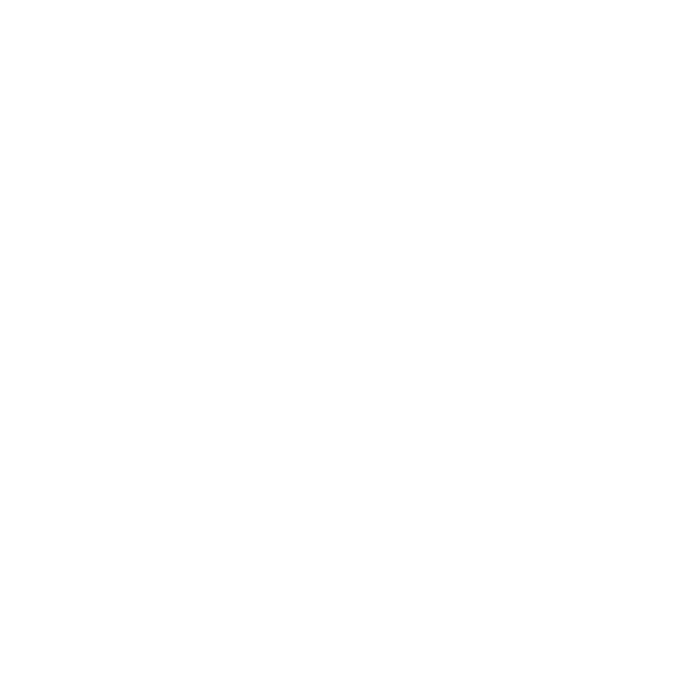活動日期: 20.09.2013
活動地點: 觀塘海濱長廊
講者:
陳嘉銘先生(文化研究苦力)
潘達培先生(資深電視紀錄片編導)
陳:我們從事文化研究最喜歡了解權力關係,例如在虛擬世界中,我們正在面對一個怎樣的權力?我們在那個世界可以掌握甚麼權利?我一直有個疑問:當我們使用網絡空間的時候,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呢?我們可以很自主地參與一個批評的過程,也可以很自主地參與一個道歉的過程,甚至可以一改常態,發放完很多負能量以後再跟大家道歉說「我不應該發放那麼多負能量」…… 那種不停反覆的語言是一種權利,還是需要一個機制來控制呢?說得具體一點,某個院校曾有人提倡過是否需要有人控制網上的空間,讓同學在網絡平台留言時不要那麼多匿名,不要有那麼多負面的想像,但終於還是沒有成事。那我就想將這個問題留給大家,也問一下潘達培,究竟一間院校是否需要這樣一個機制呢?一個國家是否也需要這樣一個機制控制網上的言論呢?
潘:我想大家看《公民部落客》的時候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就是開場時佐拉一直說他生活在一個謊言的世界,所有新聞都是假的。例如我們讀新聞系的時候,老師常常對我們說俄羅斯《真理報》就沒有真理,而我們的《人民日報》就沒有人民。當佐拉談論那些官方媒體、主流媒體其實只有謊言的時候,在一個體制裡面,年青一輩的記者其實正在做甚麼或者在經歷甚麼呢?
當年溫州動車相撞事故,我一直在追看微博的消息。頭七的那天,有很多內地體制內的報紙,都出了他們的特別版報導。但因為中央宣傳部一聲令下要減,當晚所有報紙的編輯室哀鴻遍野。當晚我在微博上一直看這些年青的記者怎樣寫,我讀其中一些給大家聽。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日,其中一個是《廿一世紀經濟報導》的記者,她這樣寫了一句:「今–天–全都白幹。」「今」後兩劃,「天」後兩劃,「白幹」是很強烈的意思。她說:「我對不起今天耐心接受我採訪的那些採訪對象……對不起。」這些是在體制裡面年青記者的心聲。第二條是《新京報》的記者:「終於下夜班了,禁令,大調版,手忙腳亂……大雨滂沱,真希望一個雷,劈死下禁令的人,劈死所有企圖掩蓋真相的人……當街劈死。」我猜,主流傳媒,尤其是大陸的傳媒,面對著這樣的局面:這一大群很有心去做新聞、希望博取更大的空間、向著真相方向走的年輕記者,甚至是一些是像我這個年紀,四十多歲的記者,其實都會感到很挫敗的。希望大家可以知道,當我們寄望這些公民記者可以多做一點事的時候,我們要看看在主流傳媒中打拚的記者其實正在處於怎樣的狀態。那一晚我一直看著他們怎樣說,其實很心酸,我作為在香港的行家之一,覺得做主流傳媒記者真的很辛苦⋯
陳:你可不可以轉做公民記者?
潘︰我看這件事時會問很多問題,例如中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社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公民的權利,人民是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當然憲法上所寫的和現實有很大的差距,我的問題是,其實西方都有很多類似的謠言存在,即是在網絡上發放未經證實的消息,但是未看到西方有特別的法例去制止。最近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警察院推出來的法規,就是要下重藥去制止網絡上的謠言。他的說法是現在大陸有這樣的情況,有人故意製造謠言然後對企業或個人進行敲詐,這個條例就是要壓制這種行為。但這個條例出現的時候,一殺就殺盡了所有好與不好的,真與假的消息。問題在於現在大陸的情況是有主流傳媒,但主流傳媒又不像香港,他們的主流傳媒可能都不是向著甚至是遠離了真相。那麼,究竟公民部落客又或者公民記者在扮演甚麼角色呢?他們是怎樣抗衡內地主流傳媒中不報導真相的情況?其實他們就靠近以謠言的方法去做。
陳:《公民部落客》中的兩位主要人物,他們開初的心態並不是想要當記者,或者不是真的要做公民記者,而是有點無心插柳。周曙光有點像想揚名,他一開始第一句就說「我想出名」。他要出名就要用一些奇情的事件,甚至用有趣的包裝去報導一些意外,從而引起人注意,但同一時間他可以站在一個比較邊緣的位置來挑戰體制。另一位亦然,其實他也是看到有人受傷就拍下來,放到網絡上被傳開來,就變成了他好像也常常站在一個邊緣位置去看這個體制的事情。我想問,不知道潘達培你接觸內地的公民記者時,看到他們是怎樣為自己定位呢?他們是如何看自己站的這個位置、這個角色去對抗權力呢?
潘:其實當他們面對如此大的國家機器時,他們用的方法就好像劉伯溫在中秋節獻計給朱元璋,把字條塞進月餅,再把月餅分派出去,用一個流言、謠言的方法來對抗。
陳:國家機器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但周曙光的報導又好像比較小,他是一直做,不知不覺把事情做得愈來愈大。
潘︰其實他是不自覺的,我肯定他沒有想那麼多。但你知道我們作為記者,發放一個消息前,起碼要有兩個信息來源來確保消息的真實性,這是有必要查證的。但對於網絡的信息而言,則不需理會消息是否已經證實,總之先發放了再說。或者以新聞報導的角度而言,這不是一個專業的做法;甚至因為這是未經證實的,所以算是不符合道德的做法。
陳︰你剛才說到主流的記者會因現實感到失意,其實主流記者和公民記者之間會否也有正面的互動或合作呢?
潘:其實很多時候,當內地的主流記者在自己的報紙上發放一份稿時,他就會把稿分成幾份,放在自己的微博上。久而久之,差不多同一時間在他的微博上寫他在現場所看到的事,同時正在做他要做的稿件,再寄到編輯部於報紙上刊登。當然這樣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究竟這個記者是為了他自己做一份個人發放的信息,還是他以報章記者的身份發放呢?到了某個程度,其實他自己也混淆,我想這情況在香港比較少見。
陳:在場的朋友有沒有甚麼想說的,或者有甚麼話題想提出來大家討論一下?
觀眾:你好,我想說的情況是香港的主流傳媒和民間記者或者獨立媒體其實是有合作的。例如06、07年的天星皇后碼頭運動,初時主流傳媒都不太理會保育話題,抗爭受到獨媒關注後,那些主流報章、電台、電視台都一窩蜂來做這話題,好像製造了一個風潮。當時兩方的互動不錯,然後這幾年一直都有一些合作。獨立媒體如朱凱迪就經常告訴我,他常常把資料送給主流的報社,好讓他們去跟進。獨立媒體負責發掘一些材料,主流媒體就進行深入一點的報導。假如事情得以曝光,主流媒體就會追蹤,香港主流和獨立媒體合作的情況不俗。我會有點不滿現在的新人,他們大多喜歡即時的、珍貴的、有噱頭的資料,一定要有花樣可耍;若只能平鋪直敘報導的話,他們只報一次就算,並且日後不再來往了。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是需要有Facebook、獨立媒體和以前的博客,把我們應說的發放出來。因為主流媒體不可能把新聞的所有層面都概括到,有時候獨立媒體報導前都要先衡量一下,很多細節不能馬虎。但在自己的Facebook和個人網頁上就可以盡爆心中情,這就是互相補足。我想說香港還可以有獨立和公開的媒介來說自己想說和關注的事,但在內地其實很難。我很少去內地,但我也有關注他們的情況,他們玩擦邊球的技術實在是出神入化,甚至香港根本不會想到這樣做。
潘:玩擦邊球是其次,重點是內地的狀況很扭曲。你說香港兩方的合作,我當然不喜歡用「合作」這詞,我覺得是誤導,兩者合作下發放出來的新聞可信性很低,好像合作製造一些事情出來。其實大部分的主流傳媒在重要的事件上,雖然也有很多失誤,但那些年輕的記者都嘗試在有所限制的傳播媒體空間內將一些民眾的聲音發放出來。他們仍然在很多事情上被壓制得很嚴重,而且正因為這種壓制,令那些真消息或說是被壓抑的消息流到微博,流到那些公民記者身上:發一條微博,用謠言的方法傳播。
用謠言的方法傳播消息,當然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當然是那件事被曝光了,但有很多未經證實的消息也可能成為謠言般在滾動。我們可以想像,內地的社會既需要一些真實的東西,大家同時也浸淫在一個謠言滿天飛的社會裡,這樣其實是很不濟的。香港暫時未到這個地步,也不希望會發生。我真不想到最後所有在香港發生的事,所有我們認為要得到報導的信息也只有在Facebook發放。你知道這些信息好像一個個浪般撲出去,其質量和可信性等都會備受質疑。
陳:剛才我聽到那位朋友說可能會憂慮香港到底會變成如何。你們可能都比較樂觀,提到皇后碼頭的事件是由主流媒體和獨立媒體一起互動做出來的。我想到另一個例子是「佔領中環」,事件由戴耀庭在信報上寫的一篇文章而起,後來主場新聞訪問戴耀庭,事件便熱起來,可見這也是一個主流媒體和獨立媒體互動的結果。問題是後來報導的空間好像收窄了很多,而且不只是主流媒體的空間,當中是否出現了一些勢力或權力,在大家不知不覺間滲入甚至控制了媒體呢?我想問一下大家是否擔心?從這些現象來看,香港的言論空間是否愈來愈小呢?
觀眾:我反而不擔心這個問題,而是很多時候焦點被模糊了。問題是現在的報章常常寫「佔領中環」,佔了很大的版面,變相可以報導同時間社會上所發生的其他問題的空間就縮小了,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的。有一個很大的所謂運動或議題,就蓋過平日要做的小事;只顧追求那些大事,但到頭來又可能只是一場空,而平日要做的事就無人去做。那時候我們就跟陳雲爭論這個問題,那時陳雲說保育菜園村,反高鐵運動失敗的原因是保育人士只懂和街坊一起走難行的路,不懂耍花招進入主流或者進入建制去改革制度,不懂勇武抗爭、搞革命。但現在的問題是有時候香港沒有理性的討論和判斷,沒有反思,所以我覺得整個問題反而不是要擔心言論自由會收窄,而是大家現在有一種惰性,懶惰了。
潘:我這樣看,當然我們有言論自由,即是我們可以表達意見,不會因言入罪。反過來說,若然你會因言入罪,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指標來衡量一個地方的言論自由。回頭說這部電影中的兩個人,他們拍攝的時候是08、09年,即是他們最活躍的時候,那時候他們的做法並不違法,但我可以告訴你,由今年(2013年)9月開始,他們正在做的事,尤其是他們那麼有名,很容易被人入罪。因為在那新的謠言法裡面的刑法寫明,如果那個消息是假的,而你放上微博之後這個假消息被轉載有五百次以上,你就可以被量化成為「犯法」了,那是很容易中招的。你想想政府以這種方法處理謠言,這個社會其實很恐怖。當然第一個恐怖是這個謠言滿天飛的狀況本身,而香港會不會步內地後塵呢?
大家再想想,政府要處理謠言滿天飛的狀況,其實只要開放所有主流傳媒,令他們不再是官方喉舌,而是成為人民喉舌,為人民發聲,這可能才是最根治謠言出現的方法。但我想以今日共產黨的胸襟他不會這樣做,亦無這樣的膽量去做,因為一旦開放報禁的話,我想第一個倒台的、被猛烈批評的就是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所以他不敢這樣做,也想不透該怎麼做,於是乎訂立很多法規嘗試控制民間的謠言,就像規定以後月餅不得製造多於五百個一樣,可以如此荒謬。在那麼荒謬的情況下大陸這樣的狀況繼續下去到底會如何?而這種狀況離我們很近,他的情況如此混亂,那我們又如何呢?我有時候都會轉發內地的微博,那我會不會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訊息被人轉發了五百次之後,然後過境時有人拉著我說:「潘生,對不起,你犯了法,我現在要帶你到公安局。」但我很明白他作為管理者都覺得事態嚴重,也會很煩惱。煩惱的是他知道網絡世界有些東西是無可救藥的,說甚麼都會流傳開去,網絡流通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情況。但同時知道有很多人其實在利用這些空隙,以謠言來勒索一些機構。他們先把謠言發放出去,然後勒索以及恐嚇說:「如果一下子有幾十萬條訊息轉發,那你的企業就有難了,要滅去負面信息就給錢。」這些事確實存在,所以網絡罪案要管理之餘又要留意政治禁忌,但你該如何處理呢?怎樣管理謠言呢?到底謠言可不可以被管理?
現在內地用的手法如此決絕,社會亦處於高壓狀態,這種情況是很容易亂套的。我的感覺是愈壓就愈亂,也很擔心愈亂的話會為社會帶來很大的震盪。我相信這股熱度香港也能感受到,而這種狀況是很需要我們去留意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