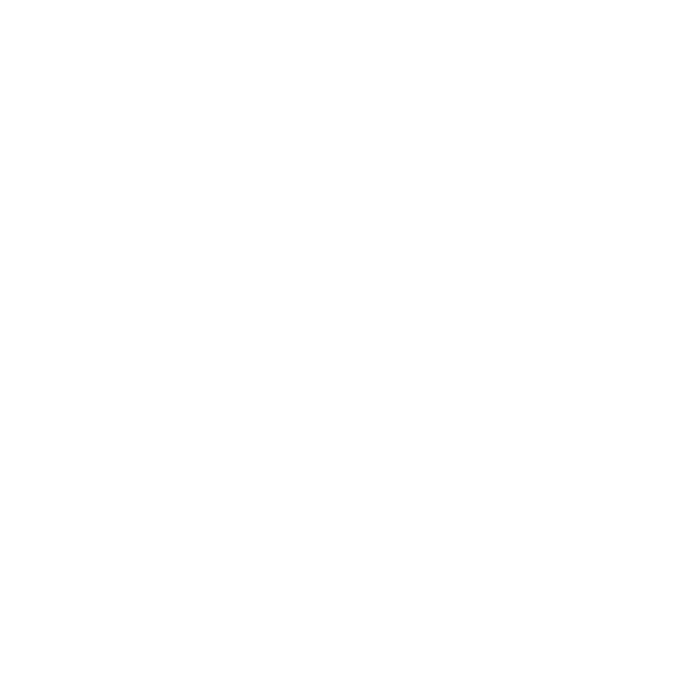在《303》的放映會中,我們繼續邀請到來自台灣的賀照緹導演與觀眾對談交流,以及介紹她的經典作品和新作。魏時煜教授除了擔任主持人外,還在現場作即時傳譯,讓外籍觀眾都可以參與其中。
主持人/即時傳譯:魏時煜教授
嘉賓:賀照緹導演
賀:拍攝前我會觀察留意哪些議題或故事在台灣當時還沒有人發覺、或是即將成為問題。也許有著所謂的「新聞鼻」,會嗅到可能即將成為問題的事件。所以當時有注意到新二代的孩子慢慢在成長,他們會面對的狀況,另外就是他們面對的問題需不需要被關注,這是我好奇的,會想知道的。所以之後我去做research, 也在台灣桃園機場附近找到一家學校,它也是一所原住民中心,因此拍攝就開始了。
觀眾:想請問導演選角的過程,為甚麼會選上片中的三位小朋友,是否班上沒有其他原住民/新移民後代?
賀:我們拍紀錄片前都會經過一個過程,以開玩笑的說法就是casting的過程。我們在field research的過程中會找影片主角。
而這次的拍攝,我先去拜訪學校校長,說明我希望拍攝的原由及意向,他就給我介紹了幾位老師。一開始就接觸到好多小朋友,大概有幾十個,當時一個班一個班的去看。在這學校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像,這就好像台灣的縮影,就是不同的民族會聚集在一個班裡,比如說移民第三代、土生土長的台灣小朋友、原住民後代,也有新移民等。而新移民都是從越南印尼泰國過來,平均分佈在每一個班裡。
而選303班級的原因是,我覺得這班的老師很有概念,比如怎樣教新移民,對他們也抱開放接受的態度。由於拍攝班上情況的過程需要跟班主任有緊密良好的溝通,而且也留意到班上的小女孩馬佩雲和另一位女孩特別活潑,因此選了這個班級。

觀眾:想請問導演介紹新移民的定義?為甚麼他們要來台灣?
賀:台灣的總人口為兩千三百萬。新住民有六十五萬,佔台灣總人口3%,而新移民小孩佔台灣25歲以下人口的十分之一,所以比重頗重。新移民通常從中國、港澳、東南亞在台灣取得居留權,並非為了工作機會,反而是因為婚姻。在我片子裡也有些很少數的新移民,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留在泰緬的軍人,之後回來台灣,所以他們的父母可能都是泰國人或緬甸人。這也是新移民組成的原因,可比例佔非常少。
所以台灣的居民跟新移民之間的矛盾,可能跟香港的情況蠻不一樣。不過我先說台灣的情況,因為香港的話大家也比較熟悉。畢竟台灣跟中國相隔一個海峽,中國對台灣的影響是有,也不少,但可能沒中國對香港的影響這麼大。
而在台灣的情況,特別是從中國來台的新住民女性,現在算是改善了,但十多年前的歧視狀況是存在的。比如說,台灣有一種菜「萵苣」,很多台灣人叫它「大陸妹」,說是因為菜食起來比較甜嫩,這別名是自中國移民來台後才出現的,所以這別名其實非常性別歧視。之後有人提出這菜應該以後統一只稱為「中國萵苣」,但有時候去餐廳點菜,有些餐廳老板只明白「大陸妹」,所以歧視仍然存在。
至於東南亞移民的部分,人口最多的是越南人。越南女性嫁到台灣的起源可追溯自二、三十年前。台灣單身男性可參加婚姻中介舉辦的觀光團,到越南選自己的新娘。過程挺奇妙的,男一排女一排,男性就自行挑選,新娘某程度上是被購買的,然後成為男士的太太,情況其實蠻糟糕,不過現在應該沒有這些事情再發生。
觀眾:注意到馬佩雲跟媽媽的自我身份認知不一樣。媽媽一直自稱是泰國人,而馬一直想把自己定義為台灣人。我想知道媽媽對於孩子跟自己對於民族歸屬感和個人身份認知想法不一會感到傷心嗎?
賀:媽媽其實是有點難過。她會把佩雲不時帶回泰國,也有跟我講過她希望女兒的民族身份認同是泰國,希望她會認同自己是泰國人。可是這樣會有困難和矛盾,因為移民來台灣是為了更好的生活,所以也期望自己及女兒能在這裡落地生根,但面對二人的身份認同差異還是會感到焦急和難過。
觀眾:看過影片後發覺跟香港的情況也可連結一起,像香港的菲律賓籍女傭,她們過來也是為了家鄉的家人有更好的生活,但在香港工作情況也挺艱苦。對於身份認知,她們是否有些像台灣移民一樣,尋求身份平等而打拼,或是一直覺得自己屬於次等階級?作為台灣移民第二代,小孩對自己的身份認知是否普遍跟父母不一樣?
賀:這問題有點大,我覺得未必跟民族身份認同有關,而是階級問題,因為這個人對此的認知會決定他們覺得自己是誰,以及個人在社會上的定位。舉一個例子,我的一位導演朋友,太太是越南人,他們的關係對等。太太對於自己的身份認知依然是越南人,而且非常清淅堅定,對於性別意識也很強,所以最近也投身紀錄片拍攝的行列。可是這樣的例子非常少,大部分的情況是,移民普遍嫁給農村生活的台灣男性,經濟基礎一般不太好,所以移民一心只想為更好的生活及下一代打拼,只為滿足最基本的生活條件。這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國家的移民身上。
觀眾:有關紀錄片拍攝的問題。片中一位爸爸跟別人爭執傷人後被起訴; 另外馬佩雲的外婆生病去世的一幕,這些戲劇性的情節都是您拍攝前早已知道因而選擇拍攝,抑或是拍攝途中才突然出現的?
賀:這些都是開始拍攝後才發生的。麗晶的爸爸因為被歧視才去攻擊那台灣人,發生在拍攝的後期部分,發生事情時我們的拍攝已經收尾結束,所以無法繼續跟進後續的事情;而佩雲外婆在她們剛從泰國回來之後不久去世。以下我會分享如何在製作期之前預知會有事情發生的竅門。
這是取決於身為導演/拍攝者的我們,要不要把想拍的影片包含清楚的戲劇化主軸。因為有些紀錄片題材不需要戲劇化情節也很好看。我在構想拍攝的前期、挑選題材時已經知道,拍攝對象的生活相對充滿未知的事情和狀況,因而預計到開拍後將遇上很多具戲劇張力的狀況。
我不是故意找一個有戲劇性的題材,而是選一些預計會發生戲劇性情況的題材。有些導演會很用力去找尋有戲劇張力的題材,我就比較是著重人物、素材、議題、以及風格。風格決定了影片夠不夠震撼。相比《我愛高跟鞋》,《303》的風格比較平實,像傳統紀錄片。

觀眾:在《303》裡,麗晶的爸爸被控訴,事情後來怎樣發展?
賀:台灣有法律援助幫助家境較貧窮的原告和被告。當時麗晶爸爸的律師很糟糕,於是我請在法律援助裡面工作的朋友幫忙介紹更好的律師,因為案子是跟移民歧視有關,所以需要熟識相關案例及知識的律師。可惜最後還是沒用,麗晶的爸爸坐牢坐了三年,前兩年才出來。是「被告傷害」被判得最有懲罰性的。
觀眾:影片有其他沒放進去但重要的情節嗎?
賀:還蠻多的,在刪掉的部分其實有不同的小朋友的片段。決定不放在影片裡的原因是,如果加上的話會有節外生枝的觀感。用電腦作後期剪接之前,我會作紙上的劇本規劃,把所有影片素材都看過及梳理,就可以整理出可以發展的主故事線。這時候會有好些大塊的片段是導演很喜歡、但放進主線會變成多餘的部分,這也是導演們經常遇到的情況:明明是很喜歡、很不捨得扔掉的部分,但為了主線也不得不割愛,因為它們有時候會挷架我們(笑)。
魏:紙上的劇本規劃就是在一張張紙上寫下素材的簡述、內容,你就可以很清淅看到人物說過的話、發生過的事情,然後就可以整理出故事架構和脈絡。在取捨的過程中,一些內容很有趣、自己也很喜愛的片段,確是十分誘人但你不得不抵抗。因為不合適在影片主線中使用,只能放棄。這是一個很好的提問(笑)。
觀眾:拍攝過程中,小孩在現場面對父母發生爭執/悲傷的事情,如此沈重的事情對於只有幾歲的孩子應該會帶來巨大的心理影響,那時候您會選擇把小孩支開,還是自然而然讓事情進行下去,甚至會觀察他們的反應?
賀:我覺得不同地方不同的家庭會有他們各自的狀態。我進入拍攝的家庭已經相當長時間,也對於拍攝的孩子大概能承受到多少也有一定的熟知。一般來說,我不會故意把孩子支開而只訪問家長,因為小孩在附近跑來跑去、或是靠在媽媽腿上,這種狀態對大家來說是最自然的。這跟我們一直拍攝的方式有關,我一直都是以聊天的方式做訪問,小孩都在附近,除非小孩自己跑去外面玩。我覺得事情發生時當下最重要的判斷是孩子對事情的理解。有時候孩子的勇敢、能承受的程度遠超過大人的想像,當我對這條件有把握時,也不怕小孩在現場面對。
跟大家分享一個相關的例子:有一幕馬佩雲在泰國,她在看書。我知道她愛看書,當時沒話找話的逗她問:「啊妳在讀書喔?在讀甚麼?」然後她點答:「中文,不好好讀書的話將來會像爸爸媽媽一樣過很窮的日子。」當下我聽到心裡嚇了一跳,原來她都看在眼裡,也比我想像中更成熟,因為她這樣的年紀己能理解社會階級,以及階級跟教育的關係。

觀眾:我透過屏幕感受到被拍攝對象在生活中的無力感,感到很心疼。想請問導演您要走進他們的生活、跟他們接觸,您的感受和看法會是怎樣?感到難過的時候會怎樣處理?
賀:以《我愛高跟鞋》為例子,這影片的拍攝經歷對我的刺傷非常非常的重(笑)。我拍的每一部片都有它們各自沈重和殘酷的一面。我的內在也許有一種強韌度去接受這些的尖銳。我必需把自己打開,抱開放態度接受拍攝現場的一切,很多突如其來的強烈感受會突然衝到身上,可是我不會選擇去妨避那些感受。這可能跟拍攝紀錄片的特質有關。當抱著防衛、不讓自己受傷的姿態去接觸被攝對象,我們就可能無法真正交流。
在我拍攝的經歷中,我需要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把我的內在變得比較有韌性,同時很溫柔,卻又需要讓自己看到拍攝現場的憂傷。我們所看到的創傷、傷痕都帶著很大的力量。我把這些力量都放在作品裡。我會用較正面而溫柔的方式去轉化這些經驗,這也是我處理這些情緒的方法。不同的導演會有不同的方式,我的是用傾向女性化的方式吧。
另外讓我哭得最慘的影片是最近拍攝的。影片《Turning 18》是關於一位單親青少女面對成長困惑和傷痛。在拍攝過程中,我發覺我過於深入地進入主角的生活。剛開始我在她眼中好像一位阿姨,但後來她有時候會叫我乾媽。面對那些她需要我的時刻我會無法反應過來,卻又很悲傷。這影片無論在拍攝或是觀看,都會帶來很強烈的情緒。
觀眾:像《303》中的學校在台灣很普遍嗎?
答:不算普遍,主要是看台灣不同地方政府補助、福利的強弱有關。而在桃園就比較多新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