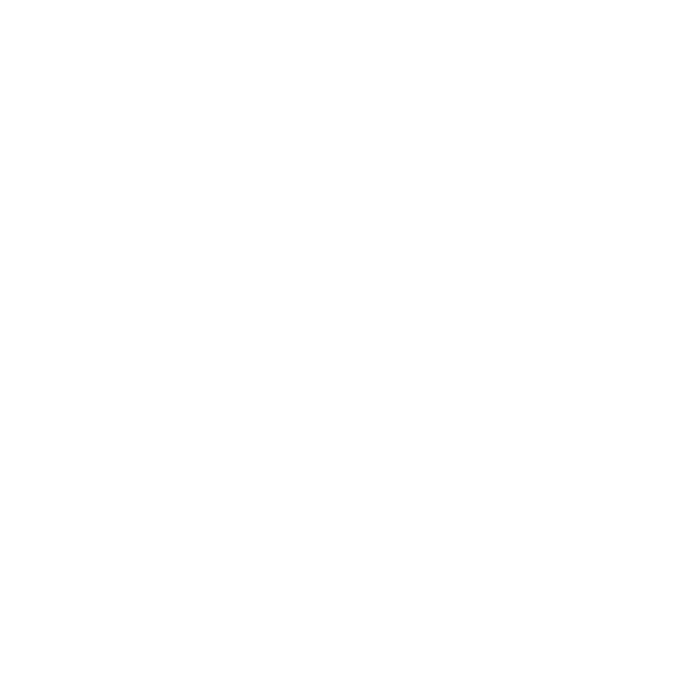12月9日及10日,我們迎來了第三回的「焦點影人」活動。第二場的放映我們請到了黃肇邦導演到場和主持人鄭政恆先生及觀眾交流,更帶來了很多深刻的討論。

主持人﹕鄭政恆先生
嘉賓﹕黃肇邦先生
鄭﹕我想看過《伴生》的香港觀眾大概比看過《子非魚》的多,昨天的觀眾應該有不少是看過《伴生》後想要重溫導演的上一部作品。有些觀眾也許已經不是第一次觀看《伴生》,這部電影在電影院也上映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黃﹕上映的時間應該是由2016年的亞洲電影節直至今年 (2017年) 的九月,大概一年的時間, 放映了接近一百場,而我則出席了六十場左右的映後談。首映是2016年十月的亞洲電影節, 十二月就正式上映,剛上映的首四、五個月,我出席了每一場公開場的映後座談,有時候有些不太晚的放映,可能是晚上八時左右,我就嘗試說得比較長一點,每次可能有一至兩小時的時間和觀眾交流。
鄭﹕本來我是想我們先談,再開放觀眾提問,但或許這次我們可以轉個形式,有沒有觀眾有些即時的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
觀眾﹕我相信這個題材是一個很沉重,也很難拍的題材,在拍這種題材時你一定有遇上很多困難,而且你個人都會有很多沉重的感受,拍攝中途你有沒有一點猶豫呢?能請你分享下所遇到的困難嗎?
黃﹕起初我是由一個義工的身份開始的,而非拍攝者。我做了數月的義工去探訪香港許多不同處境的老人家,在過程中就認識了片中這三個家庭的老人家。所以開始拍的時候,已經是累積了幾個月的相處。至於拍攝的出發點都是基於關心他們的課題、他們的故事,打算會花長時間的攝製去認識。當初沒想過只是會拍兩、三年,因為我覺得他們的生命有很多故事。我甚至想即使要花上五、六年也願意去做,最意外是當我剛開始拍攝了一個月時,松哥的太太玉梅就去世了。這件事是很突如其來的,但也明白,很多時候老人家的狀況是很難預計的。縱使平日看起來很健康,但始終年紀大,身體衰弱,隨時有意外也不為奇。結果我很快就要接觸到死亡這個課題,要切入這個點,其實開始時也有心理準備,知道終究要談到這個點,但沒有想過會是如此的快。玉梅去世後,我也一直跟著她的家庭,參與葬禮、頭七、上位等等的事情。而在這個過程中,我是會感到膽怯。
我想每個人都會有出席靈堂、白事的經歷,尤其是隨著年紀越大,經歷的機會便會越來越多。但當你是以一個拍攝者的身份處於現場時,加上跟拍攝的對象認識的時間又不長,其實我跟攝影師也是第一次有這樣的經歷,所以我自己認為在處理靈堂、關係及情感這三方面是很複雜的,因為我是要去做這件事的人,也許靈堂上的其他人會覺得這沒有什麼大不了。基於自己的角度和身份,就會無形中給了自己很多的壓力。而且一直拍下去,就會拍得越來越深入,也可能會影響到被拍攝者家庭的關係及情緒,這樣的話又應該如何處理呢?但一邊在想這些問題時,時間也一直在飛逝,我也很忙碌地拍攝。自從玉梅去世後,松哥的健康也開始惡化,那一年其實發生了很多事,所以很多時候我剛才所提到的問題,我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思索、反思。再過了半年,松哥也變成要長期住院,我也要預備下一個生命的離去。所以我想在三年的拍攝期間,起初的一半時間我是有很多負能量,卻無法憑藉我的口或身體去宣洩出來。是逐漸…大概過了兩、三年,才慢慢消化整件事。
剛才提到在上映期間,我做了很多次的座談會。其實每次與觀眾交流都是在幫助我重新組織這件事,原來我還未能很真實地消化整件事,所以我想當中的體會和滋味也跟大家一樣,需要時間去領悟,從而再思考整件事。

觀眾﹕我之前沒看過《伴生》,看之前也很疑惑為什麼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把「年度推薦電影」頒給這部電影,因為同一年也有很多優秀的香港電影。但現在看畢後,我就明白了。你拍了三個家庭的故事,拍攝了照顧者照顧老人家的過程,而你是很intensive地一個人照顧三個家庭。我的感覺很強烈,因為我也曾擔任照顧者的角色。所以我很感謝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頒這個獎給你。
而我想問的是,我昨日看《子非魚》的時候留意到只有你一個攝影師,那《伴生》就有兩名,不知道是因為經費問題,還是因為你已經一早預見到這次的拍攝難度?在拍攝這三個家庭時,有沒有時候是需要分開兩組拍攝的,或是全都是由一組人拍的呢?另外,作為一個觀察者,你和老人家的年紀相距又比較遠,你和照顧者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有沒有那一組令你印象特別深刻?
黃﹕好的,兩個問題,那第一個就是關於拍攝上的單位的問題。坦白說,因為有了《子非魚》的經驗,那次就所有事都是由自己負責,其實都拍了不少素材的。至於今次《伴生》,希望多了一名攝影師,拍攝和可處理的素材也會多一點,我也可以更專注地問問題,去了解導演這個角色。但其實《伴生》是意外地拍了很少素材,其實這兩、三年我放了很多時間跟他們相處,多於我拍攝的時間,我想這次給我的經驗是拍攝反倒成了次要。我想拍紀錄片是沒有一個標準的模式,不是每次都是用同樣的方式去做,拍攝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做法。今次這個課題比較大、比較寬,而拍攝對象的人生閱歷也比我豐富很多,我作為一個晚輩要找一個角度去捕捉他們的故事是很困難的,現在想起,我當時可能一個星期有四日都是要探訪老人院、醫院或靈堂,可能不是每次都能拍攝到素材,反而是令自己可以再了解多一點。
所以這部片的製作跟《子非魚》最不同的是,這部片沒有一個點或什麼很多的素材可以令它變成一個很戲劇性的故事,反而我是想用一個很誠實的方式,把這三個家庭認識的開始,到接下來這兩、三年的走向,有沒有什麼形式或局面的改變呢?純粹就是這樣一個心態來看,再呈現給觀眾看。其實是挺冒險的,剪接時都曾擔心,其實拍攝的素材並不多,如果作為一部長片會不會不足夠呢?我覺得事前的設計是必要的,但當事情真正發生時,最珍貴的是現場最直接的觸覺及直覺。我也很慶幸能用一個不同的手法把故事說給觀眾聽。
在過去的三年也不只是拍了這三個家庭,其實還有一條短片是關於一名104歲的老人家,她也是在過程中去世了。我一共拍攝了六位老人家,現在也只有兩位仍健在。在拍攝的過程中只有我和攝影師跟他們相處,那我認為這件事是相當好的。在香港這個步伐快速的社會,我給了攝影師一個工作,而他跟我能投入這樣的時間去和人相處、建立關係、學習生活是什麼一回事,那我想對他來說也是一個意外的收獲來的。很多人就會質疑﹕那技術上足夠嗎?所以很多時候就要做取捨,因為有了《子非魚》的經驗,這次的各方面,包括收音等,其實我跟他也是導演,他是攝影的導演,我是說故事的導演,我跟他會交替負責收音、拍攝等,是兩個人在做這件事,紀錄片的崗位其實很難有一個明確的界線。
至於第二個問題,和拍攝的家庭有沒有較深刻的經歷……我想是從幾個層面來說,一開始,譬如你最初認識或接觸新朋友也是一個比較關鍵的時候,到底要不要跟他做朋友呢、這段關係可以維持多久呢?一開始我猜想最難接觸的會是陳小姐,她由一開始便很緊張,在正式結識她前,我在老人院時已經觀察到她的個性是這樣,但意外地她說話很理性,很有紋路,緊張的性格純粹是父母使然,所以陳小姐是比我想像中易於相處的。我覺得最難接觸的是慕嚴的兒子,兆銘,因為我自己比較少接觸在這樣家庭環境成長下的人,雖然我同輩的朋友也有同樣的家庭背景,但當那個人已經不再是年輕人,他已經成長,是一名年紀甚至比我大的成年人,究竟他的心態是怎樣的呢?這點是很難揣摩,尤其我的人生閱歷沒有他長,所以開始最難是和兆銘的相處,而且他時間比較少,要上班,所以主要和他也是電話聯絡和每月兩、三次的接觸,所以就要捉緊那兩、三次的接觸去了解他。但經過了這個階段後就發現我們也有不少共同的話題,例如足球及其他男人的話題,就發現他出奇的開朗。但他和母親慕嚴的關係是的確在途中,不能說因為重聚就很愛對方,很多事情還是在學習階段,因為放下了那段關係太久。他們這個在途中的關係其實是三段關係中我最欣賞的,因為一個人可以重新拾起一段關係,然後持續地在進行、修補,那種毅力是很難得的,而且當你有一定的人生閱歷,其實你有很多其他的選擇,但你選擇回到原點。有些觀眾就覺得現在他們重聚了又是否就很相親相愛,其實也不盡然,仍然是有一種疏離感,但我看到的是就算疏離,他們仍然選擇繼續前行,到最後這段關係將來會是怎樣其實沒有人知道。
在做紀錄片之前我曾在不同的社福機構工作,接觸過很多年輕人,有不同家庭問題的人,很希望能把他們拉回正途,但當我們很努力把他們拉回來後,其實最重要的是看個人的堅持,很容易就會重新誤入歧途。在我做青少年服務時看到很多這些例子,許多年輕人都想重回正軌,但當他們的堅持稍一放鬆就會失敗。當然慕嚴和兒子的處境跟那些年輕人不同,但我欣賞的是那種勇氣和毅力,去承認和修補,而那條路是很漫長,亦不一定會修成正果,但他們依然堅持走下去,這我是很欣賞的,這段關係對我是比較有啟發。

鄭﹕比較你的兩部作品,《子非魚》就是從一個人,以一個家庭為核心,擴射出去看其他不同的小故事,當然更廣闊的層面就是看到香港的教育制度等各方面。我昨天曾提到,初看《子非魚》時尚未認識你,只是驚訝香港有導演可以用這麼低調的手法去處理一些很廣闊的題材,其實《子非魚》的題材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手法去處理,但你是從一個關心人物,以人為本的做法。《子非魚》有一部分《香港有飯開》的片段,從那個片段可以看到香港的電視節目或大眾媒體早已有一個既定公式去處理同類題材。而你則是由《子非魚》至今,雖然在觀眾眼中可能平平無奇,但你是有所選取的,亦和大眾媒體中那種煽情的做法大相徑庭,對人給予高度關注。《伴生》亦然,以人為重點,這種做法在處理此類題材上相信是很困難的。畢竟《子非魚》的主角是小孩子,相處起來較輕鬆,溝通上沒那麼多的壁壘,但基於《伴生》的題材,似乎和人物的溝通相對會較為困難。
《伴生》聚焦在三個家庭,像你剛才點出,慕嚴和兒子的片段是較少,加上他們的家只有兩個人,我覺得難度是更加大,因為只能跟他們二人溝通。拍攝出來也可以感覺到他們和其他家庭是不一樣的,他們的相處是很實際的,到醫院覆診等等,導演對人性低調的關係就透過這些片段很真實地突顯出來,
黃﹕如果說在電影的八十多分鐘內,惟一沒有表現出來的面貌就是慕嚴在私家醫院內的片段。其實能容許我拍到這個程度已經很感謝,因為香港拍紀錄片真的很困難,基於私隱度和要保護當時人。現在香港已經很少人願意打開門讓人作客,更何況拍攝,但我覺得又不可以強人所難,因為拍紀錄片最重要是互相尊重,畢竟影片完成後也會對當事人造成影響,所以我很重視這個原則,也深明不能強求。出於這個原因,所以拍攝對象的家庭片段會較缺乏,因為和他們的關係未達到那個階段,這樣的確會令一部紀錄片的論述不夠具體,但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不是每樣事情都要做到極致,紀錄片是有不同的面向,惟有運用自己有的素材去說故事。
鄭﹕那和《子非魚》相比,《伴生》的挑戰度……
黃﹕我想說,其實鄭政恆先生是《子非魚》成片後,第一位觀賞及撰寫評論的人,當初讀畢他的評論也很震憾。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當導演、拍電影,這些對我來說是意外的收獲來的。我和在旺角街頭賣球鞋、傳菜的普通人無疑,就是因為如此普通,所以我對人的閱讀能力及相處是很深刻,很關心人的故事和成長,所以我的作品也是關注人的成長。因為我覺得人的成長是很珍貴,所以我拍《子非魚》時沒有什麼大的意義,只是我走進一間小學,跟一群小學生相處、玩樂三年,那段時光是很快樂。但是如何維持生計呢?我就在外頭一邊做其他工作,所以拍攝紀錄片對我來說仍只是一個副業或興趣,不過為什麼會持之而恆地做下去呢?如我剛才談到,我曾到很多社會服務機構實習及工作,其實我一直都在找一個適合自己的方法把我觀察到的故事和大家分享,或和大家一起思考某些問題的解決方法,最後發現也許影像是較符合自己的平台,加上大學時曾接觸過紀錄片的製作。我這個人是不適合從事新聞的,因為我討厭速食的東西,如剛才鄭政恆談到,媒體有它們一貫的流程。很多時候花了很長時間和很多心力去訪問人物,做完一篇報道,但完結後就不會再理會他們日後的發展,那究竟那個人所說的是真的嗎?或單純是表演?我對這些報道抱持很多懷疑,縱使我是讀新聞系,但我並不太喜歡那種做法。但作為一種傳播媒介,它有它的功能性及存在的必要。
於是我就跳出這種模式,發現原來我享受的是陪伴他人一起成長、一起經歷,那種經驗和價值可以豐富我的人生,就是這個背景和性格使然我就著手拍攝《子非魚》。拍攝期間我也沒有想得太深入,也不知道拍攝完下一步可以怎樣做,是聽了大家不同的意見及評論,說這部片原來探討了很多議題,甚至是成年人的問題。於是我就回頭重新閱讀這部紀錄片,再學習,所以紀錄片是一個持續學習的過程。
至於給自己的第二份功課—《伴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這個議題其實我關心了很長時間。從一個中學同學的葬禮,到自己祖父母長期病患的經歷、家人要安排他們身後事的壓力、無處宣洩的感受,我作為一個晚輩把所有事都看在眼內,卻沒有傾訴的途徑,但一直也很想把這些感受表達出來。透過拍攝紀錄片,講述他者的故事,好像較容易表述自己的感受。所以每次拍攝都是紀錄他者,然後再反思、投射自己的過程。

鄭﹕當這部片子上映後,我覺得社會的回嚮是細水長流式的。而你的作品給我的印象是很不功利化的,不論是題材或處理手法也不是要立刻達到某些實際的目的。加上要和拍攝對象有這麼深入的交往在在華人社會中是需要花上很長的時間,才能讓他們打開心扉,談論生老病死這些深刻的話題,所以我覺得你有一種細水長流的耐性。碰巧這部紀錄片面世後也是有一種細水長流的反嚮,有很多場的放映。我相信六十多場的映後談中觀眾一定有很多回嚮,或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感覺細水長流這四字很貼切地描述了整個過程,以及日後的回嚮。
黃﹕是的。其實至今我仍未適應,不管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獎項,或觀看的人次,以及收到的讚譽等等,我還在消化中。不過我有兩點想強調﹕首先紀錄片是有其存在必要,但它畢竟是一個紀錄,一個故事。當我明白了這一點後,我就覺得要好好利用座談會的機會,最初的十場八場,我主要還是跟觀眾分享電影拍攝的點滴,但之後的數十場我就決定要談及一些電影以外,和大家切身的議題,不論是政策或資訊也好,要透過這些時間分享給大家。我覺得閱讀完一套電影後,觀眾如果能吸收更多關於長者政策的資訊,整件事就會更加圓滿。所以我也不知道應怎樣形容我現在做的這件事,有些人覺得我其實在做研究,只不過是透過電影媒介表現出來。
《子非魚》和《伴生》這兩個故事其實沒有結束,我認為生命的故事是不會就這樣就結束。《子非魚》之後,我仍然在關心青年人的成長,即使不是以紀錄片的形式。以後的電影作品可能也是以這些題材為主。至於《伴生》之後,安老的議題其實很重大,奈何香港在這方面的確很落後,我也有和一些研究長者政策的朋友不斷地交流,他們提供了很多資訊給我,例如為什麼香港老人院設計得好像醫院一樣?原來是因為沿用了美國那一套軍營式的設計,所以與北歐那些空間寬敞,感覺真的是給長者養老的設計很不同。這些事背後是有其原因及歷史,要先了解然後再針對這些事提倡改變。這一年來我就不同跟這些朋友交流,如果我接受了新的資訊,我就會在座談會和大家分享。最初我在這方面的知識是比較貧乏,可能只是認識所謂的「衰仔紙」或一些寧養政策,但慢慢發現原來有很多層面可以討論,就是透過座談會,看大家向我提出了什麼問題,再將這些問題拋給下一場的觀眾思考。其實這六十多場的座談會帶給了我很大的滿足感,亦猜不到最終會演變成一件這樣的事。我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對與否,只知道這符合了自己的心意。也許可能我下一個關注的題材會截然不同,但希望所接觸過的題材會繼續滾下去,不論是我由這方面也好,還是由觀眾主導,最高興的是大家能共同孕育這件事。
鄭﹕你說到今年九月終於完成了這個使命,那結束後你有失落嗎?
黃﹕其實這一年過得很快,每個星期有幾日都要晚上七、八時到戲院準備,然後中途又客串,在一套十三集談論生死問題的節目中擔任主持,做了很多與這個題材有關的事情,不知不覺就到了十二月。至於失落與否,我反而是感到我做的事仍未足夠,希望能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多。剛才說我以前不是做這方面的東西,直至現在變為專注於這個範疇,同樣地是因為覺得時間過得太快。我從二十多歲時開始做《子非魚》,而現在我已步入三十歲,其實我只不過完成了兩部作品。但已經過了十年,就想反正也回不了頭,倒不如繼續做,做得更多,這一年對我而言,是心態的轉變上很重要的一年。
鄭﹕回到《子非魚》,現在那群小孩子的故事又如何呢?
黃﹕他們的故事還在繼續,我跟黃俊修是挺好的朋友。他現在就讀中二了,認識他時他還是一年級,剛留級一年,拍畢《子非魚》時就剛好是他們三年級開學禮,亦陪伴他們度過了中學放榜及小學畢業禮。畢睹他們成長是一件很開心的事,他們現在長大了,樣子也變得很不同。不過小孩子是變得很快的,記得那時他們二年級,我就和其中一名小朋友說我以後沒有這麼多時間陪你們玩耍,小朋友就追問原因,顯得很依依不捨。到了他們三、四年級,我又回到鮮魚行拍攝時,他們已經變得很冷淡,之間的關係就是如此軟弱。(笑)
但最震憾的一件事是他們六年級時,當日是他們的結業禮。在小息時,黃俊修就要我教他寫一張感謝卡,原來學校一名男主任要榮休,所以他想感謝他,但他又不知道該怎樣寫。此時他的同學走進來說一起寫吧。然後同學又問黃錶在哪裡,原來他們二人合買了一隻錶送給主任。言談間他們談到送錶的意義,黃又說因為主任經常生病,所以退休對他而言是一件好事,說著說著二人又開始鬥嘴。
卡寫好後我陪他們走到教員室,我就好像家長般站著遠處看他們。他們把主任叫到教員室外,然後就把禮物和卡送給他,那一刻我就感慨原來他們已經長大成一個溫柔的男生。因為我不是當老師,所以很少有這樣的陪伴一個人成長的機會。但那一刻就覺得原來這個經歷是很特別,尤其我跟黃俊修本來就不認識,之間毫無關係。
鄭﹕昨天我也提到《伴生》的結尾與《子非魚》開始的地點是一樣的,也是在尖沙咀海旁,然後鏡頭向著香港島。我覺得這個鏡頭很能闡明你的作品包含著對香港一個很廣闊的視野,轉而去關注獨立個體,也很體現到你對香港時事及社會的高度關注,會看到社會中某些被忽略的角度。
黃﹕其實對香港具體發生的事情,我絕對稱不上為專家,也不是吸收了很多的知識,大多時我是從情感上出發。之所以會有這情感是因為我感到香港轉變得太快,每代人的處境都不一樣。從拍紀錄片得到最深刻的體會是大家都很喜歡用既有印象去判斷香港現今的狀況,認為自己的成長背景及經歷可以套用在別人身上。不單止是香港,其實全個世界都轉變得很快,但收到世界的影響,香港的改變尤甚快速。拍紀錄片亦喚醒了我自己的成長經歷。我是成長於一個較貧困的公屋屋邨,整個屋邨有三、四十座大廈,環境也比較舊,沒有電梯,要和其他家庭共用廁所。現在長大了先知道那些是所謂的老人邨,想起屋邨的環境其實對老人家很不便,也終於明白為什麼小時候會有這麼多救護車進出屋邨,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獨居老人去世也無人知曉。我就會把這些畫面和現在做的事情串連起來。
譬如拍《子非魚》的時候是想做一個對比,片中小朋友的處境和我二十年前所經歷的一樣。我們經常性說社會進步了,但為什麼還是有人在受苦,那當然所受的苦的程度是有所不同,但類型是相近。有時我跟觀眾說起自己的成長經歷,大家都會訝異原來香港有這樣的屋邨,明明只是二十多年前,就由此感到香港實在變得太快,每個人經歷的事好像一樣,但當中有很多細節其實很不同,每個人的背景也很不一樣。
所以我每次看到維多利亞港或香港一些很標誌性的地點,會覺得跟上一次比又改變了。就算大家看的是同一個風景,但看的心情可能很不同。我想做的就是紀錄這些心情,當十年、二十年後重看《子非魚》或《伴生》,可能會發現社會的確是不同了,那我當然希望會是一個好的轉變。大概就人抱著這種心態吧。
鄭﹕在《子非魚》的結尾部分,你刻意插入了那些已經升讀小三的孩子們就讀小一時的片段,彷彿可以看到他們成長的過程中時間的痕迹。可能因為是你第一部長片,所以還有些考量,而選擇了一個較跳脫及多角度的表達方式 ; 但《伴生》相對是較為簡約的,也許是主題的沉重,所以就用了相對平實的手法。
黃﹕其實兩部電影都有其趣味性。當初開始拍片時,因沒有經驗,會希望我的作品能把故事說得很好,能賺人熱淚。後來發現有很多和我關注的議題一樣的電影和電視節目,那些導演的角度其實是很單一的,很平面,只會抓住並放大小朋友的某一點,例如一定是慘絕人寰或毫無希望,所以我會刻意避開這種做法。稍為了解人生的人都知道,生命不會只是一種味道。因此拍攝《子非魚》的時候,雖然那些小孩子其實是在受苦,但他們並不自知,而我也不想剥奪了他們的童真,所以我會嘗試把這些生命的味道放到電影中,希望我的故事是有血有肉的,令大家看到生命其實有很多面向。《伴生》亦然,當大家聽到電影的主題後會覺得很悲天憫人,我最初亦跌進了這個陷阱,不過跳出陷阱就會發現雖然三個家庭所經歷的事是很黑暗,但我和他們的相處之間是充滿歡樂,沒必要把他們的故事描繪得很悲慘,那個時候就體會到生命的感覺。好像阿金和沛叔是很有趣的,所以我就盡量呈現他們日常的相處片段。如果生命只有一種味道,其實是沒辦法捱過一輩子。「苦多於樂」,正正是有這些微的樂,才能支撐到這麼多的苦。拍這兩部紀錄片時就是希望讓大家看到這些真實的面貌,這樣大家看東西的角度才更闊。
我常常覺得,香港媒體的角度是比較窄的,不能以多種面向去閱讀一件事。縱使《子非魚》和《伴生》是一項很普通的project,我也希望可以提供不同面貌讓大家了解那件事,我覺得社會應該要這樣補充才會完整。
鄭﹕《子非魚》的確是抗衡了一些很單面向的兒童貧窮問題的探討,《伴生》也抗衡了一些我們很忌諱的議題,兩者都帶有抗衡的意味,抗衡大眾的一些既定想法。那現在還剩一點時候可以給現場的朋友發問。

觀眾﹕我第一套看你的作品就是《子非魚》,我覺得兩部紀錄片都展現了你樂觀的性格。雖然兩部談討的題材都很沉重,但《子非魚》是笑中帶淚,《伴生》則是淚中帶笑。至於我的問題……因為我收藏了《子非魚》的DVD,所以也想知道《伴生》會發行DVD嗎?另外也想知道你下一部作品是關於什麼。
黃﹕《伴生》大概會在明年發行DVD。至於下一部作品,其實已經進行了一年左右,這次的題材比較特別,是關於環境的,跟我以往一直做的是不同面向。我也不太習慣談論進行中的計劃,不過希望能成事吧!我有好幾個議題都想做,希望能持續地跟大家分享。
觀眾﹕我想問的是,你在拍攝時是如何跟被訪者建立長期又互相信任的關係?
黃﹕有幾種方法的。像我現在拍的那一部就是不斷被罵,接觸對方時會被罵,拍照又會被罵,什麼類型都有的。怎樣說呢……我想我仍然受惠於自己的年紀,所以想跟人聊天也會比較客易,加上自己以往是做售貨員的,比較擅長與人溝通。而且我做的又不是什麼大的項目,不會在電視上看到。所以很多人就會比較願意結識你,之於會不會進行拍攝就是另一階段的事情。
因此第一個階段也未必會談到拍攝,純粹想多了解對方,當中包括不同年齡層的,從小孩到長者都有。我會經機構作探訪,或有時就在街頭跟人聊天,的確是需要很厚面皮的,畢竟就算你想主動關心人,不是每個人都需要你的關心。我以前在大學有一份習作是拍攝跳街舞的人,他們與我的年紀差不多,但是很兇惡、強悍,不容易接近他們。當我表示我是為了我的功課而想多了解他們,他們就會反問﹕街上這麼多境況悽慘的人,為什麼不去拍攝他們?總之他們的口吻就很囂張。
但同時亦令我反思﹕世界這麼大,為什麼我會對某些人特別有興趣?為什麼我會特別想拍攝某一個群體?一定是有原因的。如果沒原因地去做,那只不過是一個工作。但對我而言,紀錄片是一個創作,是關於你和拍攝對象的一個關係,至於這個關係是什麼則由你自己衡量。但你必須有興趣,甚至是喜歡這個關係,才能孕育出一個紀錄片。而隨著自己的閱歷漸增,有興趣了解的對象亦越來越多,然後就會朝著這些對象再慢慢發掘。但我們並不是要從上而下地結識對方,而是自己有某些事情想多學習,透過對方去了解更多,平等地建立一段關係。不過很多時候都會失敗,所以如果你認為值得的話,就要很努力地栽培這段關係。

觀眾﹕昨天我就和我15歲的兒子觀賞了《子非魚》。當然很多媒體也報道過香港的貧窮問題,但我認為你在《子非魚》的處理手法是很舉重若輕的,或好像鄭先生所說的「細水長流」。觀賞後回到家,很多片中的畫面都不時浮現在腦中,我很欣賞你運用小朋友的說話來反映出你想呈現的一些事,或小朋友真實的情況,使我們可以很深刻地討論,以及透過影像讓下一代明白我們應多關心基層的人。
我的問題是﹕在片中,有一個較瘦削的小男孩說了因為爸爸家暴,他和母親因而離家出走。當你詢問他感受時,他說挺高興的,電視劇的情節也是這樣。聽罷我就思考,其實這些小朋友是否也會掩飾自己的不安或一些不愉快的經歷,你和他們相處時會有這種感覺嗎?謝謝。
黃﹕我認為這個問題,家庭教育是最為重要的,特別是對這個年紀的小孩子。從出生到那個年紀,他們主要的學習對象均是母親。他們會全盤吸收母親的性格及說話的方式,但吸收了以後他們都未必了解箇中的意味,往往也是一知半解。與其說是掩飾,倒不如說是一知半解。
很多創作人認為小孩子特別純真,喜歡問「為什麼」。但在《子非魚》你會發現多是由我問「為什麼」,那些小孩子反而會說「就是這樣的啦」,其實他們也回答不了背後的原因。
整個社會及他們的家庭在他們小時候已經不斷向他們灌輸這種價值觀,他們則照單全收。當然一些富裕家庭的小朋友的遭遇就很不同,從小就可以上不同的興趣班,學習不同的技能。但對一些條件沒這麼理想的小朋友,他們的知識或價值觀就只能從家人、電視或街上的人身上吸取。另外,看《子非魚》時也會發現是缺乏了父親的角色,原來一個家庭沒有父親的存在是會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會缺乏了一個平衡。就像片中,如果母親是新移民,知識又不多,加上是老夫少妻的背景,他們灌輸給小朋友的那套價值觀是很單向的。據我的觀索,當然不一定準確,但其實片中很多小孩子也希望有一個能作為他們榜樣、偶像的父親。然而如果一個家庭不完整的話,就會發生這種失衡的情況,而價值觀亦只能單一灌輸。那我覺得這對小孩子來說是很不幸的,因為他們尚未有條件及機會去學習,從一開始就已經被困在這個局面,所以為什麼社區組織和學校的把關應該要更加用心呢,就是希望能透過教育改變他們。
然後就會發現香港很多的教育政策是很奇怪的,學校處理的壓力又很大,未必能像鮮魚行的老師般那麼全神貫注地關注學生,因為鮮魚行一年級的班別只有一個,一班二十人,如果只有二十個學生都已經有這樣多的故事,試想一些收生正常的學校,一級有四、五班,老師要應付這麼多學生,他們又會否有這樣的心機和力氣去認識及關心每一個學生?其實真的很困難。我們談論了這麼多的問題,會發現當中是層層相扣,整體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不能只針對單一方向,而是需要很多力氣,整體重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