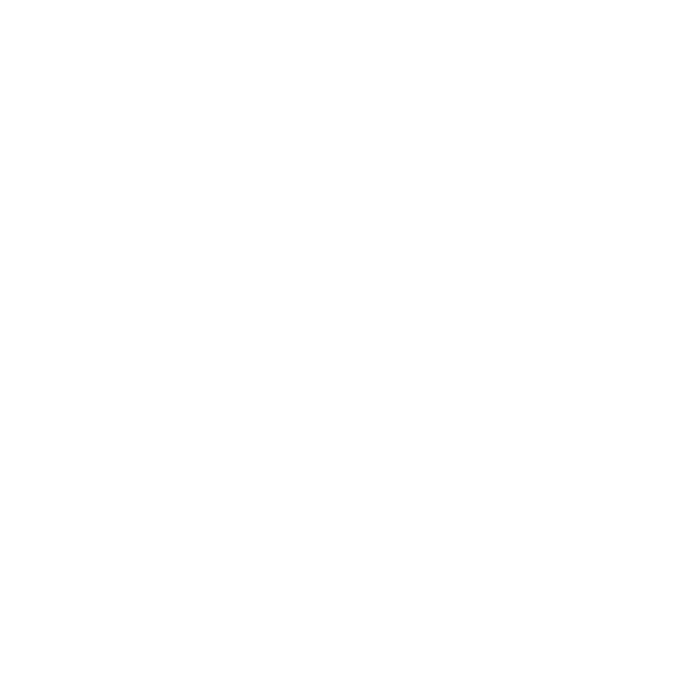在11月3日及4日,我們舉行了第二回的「焦點影人」活動。活動的首日請來了周浩導演和現場觀眾作交流,並有中大社會學系的副教授鍾華作主持。周導的號召力非同凡響,當日現場坐無虛席,《差館II》一片放映後,觀眾都急不及待,一一向導演拋出有意思的問題。以下是當日映後談的文字紀錄﹕
Q:觀眾
A:周浩導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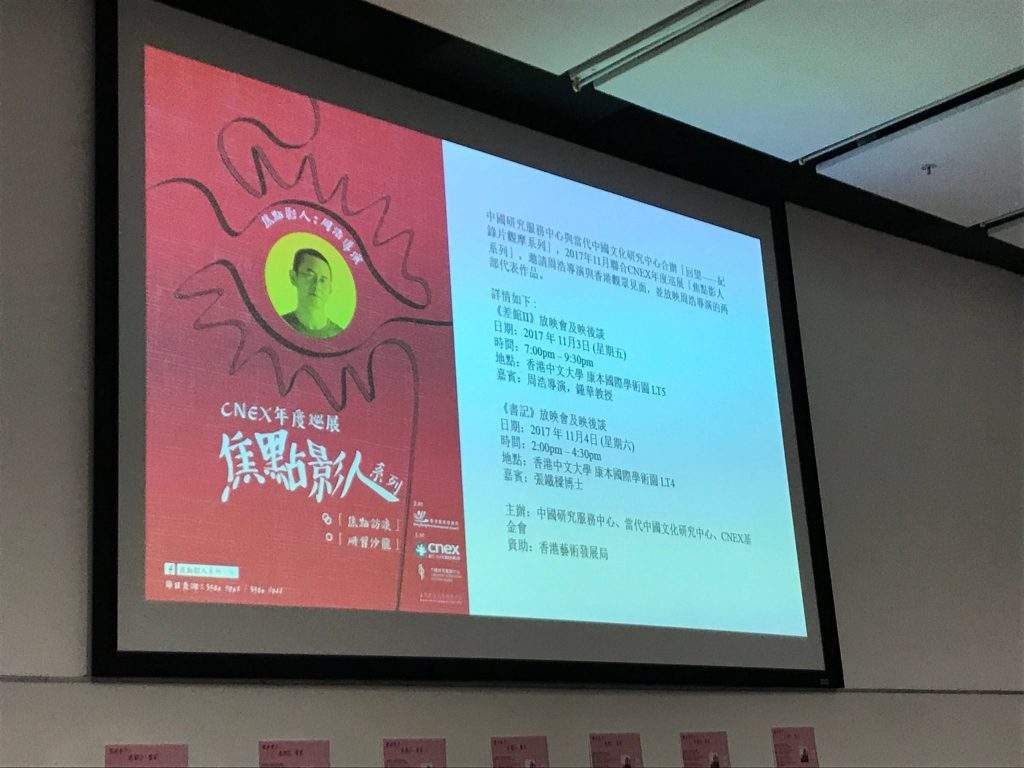
Q﹕作為香港的觀眾,片中的情節對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簡直是難以理解。為什麼那些在警察局的人好像特別開心的,這個跟我的想像完全不一樣。第二,我也很難想像為什麼您 (周導) 可以在警察局裡面拍攝。另外,我也搞不懂內地的執法部門的架構,什麼公安局、派出所、城管、警察局呀等等,您可以說明一下嗎?
A: 我居住在廣州。然後廣州火車站,大家都知道,在每年中國春運的時候,它就像是一個風向標,就是說,想要知道中國春運時的狀態,只要透過這個廣州火車站的觀察就大概可以知道是一個什麼的狀態。在2010年的時候,因為我住在廣州嘛,我就想,我應該要去拍攝廣州火車站的春運 (情形) 。每年春節,打工的人都要回家,而廣州火車站的人流最高峰時可每日達大約三十萬人。我當時就想拍廣州火車站的春運,但廣州火車站聽到我要拍一個月時就被嚇到了,因為拍攝時他們要派人跟著我,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所以火車站拒絕了我。然後我同時也給公安局提了份報告,結果春運沒拍成,但是拍到了差館。這個有分《差館I》跟《差館II》,《差館I》就是2010,第一年拍的。第二年我又去了,這次大概拍了十天的時間吧,其實我還想一直拍下去,但後來公安局覺得我拍跟想像的不太一樣,所以就沒有進行下去了。
在中國,中央有一個叫公安部的地方,像司法部一樣是一個部委的機構。在省裡面就有公安廳 ;在市裡面,有公安局,然後再往下走,有各個區,譬如說,廣州市越秀公安分局,越秀區就有一個公安局。然後區再往下面走就有派出所,派出所就是比較特別,它的轄區比較細,片中的派出所負責的就是那個火車站外的廣場的治安,裡面是沒有居民的。這個派出所大概是全世界每單位面積警察人數最多的一個派出所。天安門也是類此的,它就有自己一個天安門分局。這大概就是中國的行政架構吧。
這片子為什麼叫差館,其實這個詞在廣州是沒有的,香港人很喜歡說差館、差人嘛,這個本身是一個帶有地域特色的詞,我就想用這個詞來表述這片子,因為我覺得裡面的那些警察就是差人嘛,差人就是有一份職業,就是因為他們的職業跟我們的不一樣,他們就是警察。這部片子就是想描述普通警察跟民眾之間的關係。
其實在中國拍了很多片子,甚至在全世界很多的範圍,包括香港也是這樣的吧,其實也沒人說你不能拍,很多時候是我們連這樣的努力也不願意去做,覺得那個是一個禁區,不能拍的。其實很多地方只要你去努力的話,而且你也是不懷惡意地去拍的話,我覺得是能夠拍到的。我一直覺得人和人之間,是特別渴望別人去了解你的,你之所以不願意給人家拍你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擔心別人的介入會對你的生活產生影響,我覺得只要把這種觀念打消的話,就一切都有可能。
主持人﹕那為什麼片中被關起來的人會這表現得那麼開心呢?
有人曾經跟我說,說我的片子拍得不夠真實,我說為什麼不夠真實,他說因為他沒看見警察打人。我承認警察會打人,但如果你用一種這麼貼標籤去看一個職業的話,那其實你在進入之前,在觀看之前,就已經帶著太多的成見。這個世界之所以有這麼多的矛盾跟衝突的原因,就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不理解與貼標籤。其實你為什麼認為在監獄的人、被關起來的人就一定要哭呢?他進去以後待幾分鐘就出來了,他沒有必要哭呀,我覺得這是一種狀態,這也許是你對這些人的一些先入為主的一個判斷吧。我也不認為他們特別開心,只是他們表現出來就是這麼一種狀態吧。
 鍾華教授(左)、周浩導演(右)
鍾華教授(左)、周浩導演(右)
主持人﹕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城管在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呢?
A﹕城管在中國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職業吧,因為跟中國的地區和行政、政府的管理有關係。譬如說,中國有一個機構是國外沒有的 — 防疫站。你們知道中國的防疫站是幹嘛的呢?就好像有沙士這樣的情況發生的時候,中國就專門有一個部門管這樣的事情。甚至把愛滋病呀,一些疫防疾病的會放在這個區。防疫站並非醫院,但又是屬衛生局管。
城管呢,是因為中國社會高度發展嘛,城市有很多需要規範的事情。其實中國地區的行政可能會比西方國家的分得更細一點吧。城管就是負責整個城市的市容,一些基本的治安,小攤小販的管理,這個我也說不上很清楚,但是城管,甚至不像警察般是國家公務員。
Q﹕周導演您好,謝謝您的影片。我剛才在影片中看到一些低層民眾的生活上的問題,包括一些低層的民眾在廣場上擺賣,有可能違反一些當地的行政法規,甚至是國家的法律。但是我看的時候就有一個感覺,我覺得很多事情呀,也不算是很大的事情,我主要是跟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的一些官員來比才產生這個想法。這個片子是談公安,那譬如說,今年呢,以前內地的一位富商,郭文貴先生,他就對中國中央一些高層官員提出了嚴厲的指控,郭先生當然只提供了部分的訊息,但是那些人,作為最高層次的領導人,連一個正式的回應也沒有。所以我也想請教一下您,或者說,想知道您的感受,知道低層的民眾違犯一些當地的行政法規或法律上的一些輕微的部分,然後被拘留起來,您覺得這些事情,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些最高層次的官員相比,其實是不是不算什麼事情呢?謝謝。
A: 譬如說這個地方,這是一個廣場,像剛才說的,最高峰的時候每天有三十萬人在流動。在這個區內,它的確是有需求,像是對水,對小板凳,對一些簡單食品的需求,但是你知道那個地方,它本身就沒有一個固定的設攤的點,但它的確有需求,在這個地方,你為了不讓這地方發生過多的混亂,或者發生一些治安案件的話,我覺得政府在處理這個地方上其實是顯得比較粗放的,他會星期一到日的管理,絕對不允許設小攤小販,但實際上,很多法規跟法律的規定,它表面上是不同意你們在裡面設攤設店,但是警察在管理的時候,他其實有一定的靈活程度。我們有時候喜歡把世界理解成黑和白,但是有很多中間的這種層次。你說這地方是在管理他們,而且本身有這麼多法律的東西,譬如說,大陸的法例跟歐美的法例本身就不一樣的。在做判決的時候,也很難有一個統對的標準來衡量我們所有的行為的。你說在裡面大吵大鬧的那個人,他就是因為,在我的理解裡,就是因為他希望春節能在派出所裡面度過,他不想回家,他就想被抓。但最後被抓的為什麼反而是那個女人呢?因為那個女人大概就是有兩次、三次已經被警察逮住了,按照他們的規矩的話,這個人就應該被抓到派出所去。所以你要問我說到底什麼樣的法規是最完美的法規,我覺得是沒有的,永遠就是一種這麼模糊的狀態。這是我對派出所的管理狀況的理解。
至於你說那些權貴們的事情,我的確是無法評述,而且也不是我評述了就能夠解決問題的,我也會,就是,從我做紀錄片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我絕對不是人云亦云的人,我會用我的觀察、我的判斷,我絕對不會因為某個人,譬如你看我的片子,我也沒有非常強烈立場的,我也不認為有強烈的立場就代表所謂的正確,我會更加的,以一個旁觀、冷靜的態度看待在發生的故事。這個是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吧。而且,我覺得當你有一個立場的時候,一定有另外一個立場站在你的對立面。我也不認為這世界有絕對的正確,這個世界就是有各種力量不斷的自衡、拉扯才能往前面走。我並不認同那些事情,但也不會特別強烈的站在他的對立面。就像艾末末的片子一樣,我並不特別喜歡艾末末的片子,因為只要你在香港的街頭喊打倒共產黨,一定有人拍攝的,事實就是這樣。
Q: 周導您好,您在片子裡面就是大部分時間也在講那個警察局,就是他們在春節期間怎麼辦案,我想問一下您在中間加插了一兩個鏡頭,就是關於警察在抱怨公安局的安排之類的畫面,當時您有想過要再挖深一點這個情況嗎?
A: 啊我當然想。要是我能拍下去,拍第三年的話,我當然是想拍這群警察。其實我覺得這個世界吧,就像有時候我們會願意把共產黨放到我們的對立面一樣。其實在中國大陸生活的人都知道,當你在讀高中、中學的時候,班上成績最好的人,在十七、八歲的時候都會被收進黨。所以真的非常客觀的說,中國共產黨是由中國地區最優秀的人組成,相對而言是這樣的。
他們這些人跟我們實際上是一個整體,但是我們習慣把他們放在我們的對立面。比方說警察,當他們脫下了制服以後,他跟我們是一樣的,也是社會的一個組成部份。你說有什麼必要和一個跟你居住在同一個社會的人唱對台戲呢?所以我認為警察有他的怨言,我想每個人做每個職業都有他的怨氣,我是這麼理解的。哪有一個完美的制度。你說這片子幹麼用的呢,我說這片子是一個媒介讓大家互相了解。當你看完以後,慨嘆原來警察也不打人的呀,那你是不是對這職業有了一份更深的了解呢?這世界會因此而變得更加的和諧。你因此理解﹕哦,原來警察也不好做的。那你是不是就會對每個人有多一分的寬忍,那也許這個社會就會向善。我也不知道我一個人的力量有多大,但我是希望每做這樣一個片子的時候,能至少改變你一往的觀感。
我經常會用一個詞叫「混沌」。譬如說,你在看片之前,你對警察是有一個先入為主的判斷﹕警察嘛,中國大陸的警察就是這個樣子。但你看完這部片子之後,就會覺得﹕哦。大概也就是這個意思,「哦」。我就希望去一次又一次地做這樣的事情。
Q﹕周導您好。首先我非常贊同您剛才的觀點。然後我的問題就是﹕您在派出所拍到的鏡頭肯定不止這些,但是您展現給我們看的,只有這一個小時的故事,我想問一下您如何取捨這些人物,或者是在拍攝當中,您有沒有印象特別深的人物?為什麼?謝謝。
A﹕拍的素材肯定是大致三十、四十比一的這種比例剪出來的,剪出來的畢竟也希望它是一部電影,是一部大概幾十分鐘,不能讓別人打瞌睡,不會讓人中途離場的,也希望讓人找到趣味的電影。其實每天發生的事情很多都是有它的重複性的啦,還是從影視的角度希望它有一個完整的故事,而且拍攝的時間不夠長,大概就是十天左右,所以有趣的故事都會盡量放進去,也沒有什麼我特別避諱,不放進去的。

Q: 我想問一個關於拍攝過程中的問題,因為我注意到您採訪的對象,不管是警察或是那些低層的人,他們都很健談,而且很樂意跟您分享他們自己的看法。我想問的是,您是用什麼的態度去讓他們願意跟您打開心扉?我也注意到有很多鏡頭是從下往上拍,所以我就想這是不是其中一種方法,還是是當時場境的限制?
A﹕所謂的紀錄片,套用一句大師的話,紀錄片就是一個講拍攝者跟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這個關係就構成了一部影片。實際上,這麼一部片子,就是我把我所經歷的人生故事通過影像的方式來跟大家一齊分享。鏡頭比較低的原因是因為我跟別人說話的時候,攝影機就在我手上,就是用這個方式拍攝的。而且呢,拍紀錄片一個原則就是,我的介入是一定會對別人的生活產生影響的,只有當你充分的認識到這一點﹕我不可能做上帝,我是一個人。就像量子力學裡面說的,只要你去測量那個原子核的運轉的話,你的這種介入、這種觀察會對運轉產生影響。更何況我是一個人,我進入了別人的生活。所以我就用這個態度很坦然地去跟別人打交道,然後就希望把我所經歷的故事來跟大家分享。我一直都覺得人呀,都是特別渴望跟別人進行交流的,特別是這些在低層的人,只要你不充滿惡意、心平氣和的、不騙人,我想都有可能的。
而且被我呈現出來的都是沒有拒絕我的人,也有很多是拒絕了我的,這種部分就沒有放出來。其實就是用一種非常坦然的態度跟人家打交道。如果你看過我其他片子的話,其實這部片子裡打交道的方式也是比較容易、比較簡單的,不特別複雜。
Q﹕謝謝您的片子。在這部紀錄片裡,有些被拍到的人就說他們不願意上電視,不願意被家人看見。我就想知道,在這部片子裡出現的人,當他們之後看到您的作品時,他們有作出什麼樣的回應嗎?
A﹕這個片子裡,特別有一個片段我經常會談及。就是人做很多事情,其實我不認為你的敵人,或是說你有多少對手,其實人最大的敵人就是你自己。就好像有些人殺了人,他也會心裡害怕。其實人這一輩子,就是做好你自己,安撫到你自己就夠了。我來解釋一下,好像其中六十歲的老人,我拍他了,他在我鏡頭下無比的懷念毛時代,覺得那是一個均貧富的年代。他不喜歡鄧小平,因為鄧小平讓這國家有先富起來的人,就覺得他特別的討厭。然後在離別的時候,他告訴我他不希望我用有他的鏡頭。但是我還是把他的鏡頭用出來了,其實我完全可以把這些鏡頭剪掉。
我是這麼理解的,一個六十歲的老人在廣場賣小凳子,然後被警察抓住了,他會覺得這是一個很丟臉的事。但是看完這部片子,你們會覺得這個老人是一個特別沒面子的人嗎?我想看完以後,你們會覺得原來我們忽略了這麼一班人,我們會不會對這個人有更多的同情心呢?會不會去思考這個世界的公平性?基於這種理由,我就把這個片段放進來了。我也不知道我做得對不對。但至少我可以過得了自己的心,覺得(透過)做這個片子還是可以作一些事情的。其實有時候做片子是要把握這個分成,我不希望做出來讓觀眾不舒服,也不希望讓老人不舒服。我知道表面上是違背了我當時的承諾,但是我還是剪進來了。

Q:首先我覺得這個片子真的拍得挺深刻的,因為我是來自廣州的,這個廣州火車站的場景是我又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因為它很大,這次是第一次近距離看到這裡發生的事情,心情很複雜,也很感慨。尤其是比較近距離看見那些民警的精神狀態,他們就用一種自嘲、自黑的態度….甚至還跟那些小販一來一往,確實有一種黑色幽默在裡面,覺得很荒誕。我想到的一個問題是像那些警察談到的,長久而往地站下去會不會就沒什麼同情心呢?假如我是他們,我能不能還保留自己的同情心?大家都是人,都有人的尊嚴,在生活不如意的時候,還能保持對別人的理解心嗎?感覺也不是我向您提的問題,是您向我們提的問題,不知道您會怎麼回答呢?
A: 你沒有答案,我也沒有答案呀。我是當記者出身的,拍紀錄片也很長時間了。已經快五十歲的一個人,好像應該對這社會非常了解了, 但是並不是這樣。感覺我每次拍紀錄片,它都給了非常我不一樣的感想,這也是我一直堅持做紀錄片的最重要的原因 —— 就是它每次都會給我驚喜、驚奇。我在拍這部片子之前,從來不知道中國有這麼多的文盲,很多時候派出所要人家簽名字時,很多人不會寫。喔,原來中國社會是這樣的呀。現在我們只看見高鐵,看見微信,可是現實社會就是這樣的,這也許就是像我們這樣非主流媒體才能讓你看見的東西。至於這些問題可以怎麼解決,我覺得也很難解決的。我也不知道。每個人都想做一個改良者嘛,改變你想身處的世界,但我覺得我這輩子能當個觀察者就很不錯了,當一個觀察者,然後把我的觀察跟大家分享,至於能對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也不帶過多的奢望。只是希望我的作品能讓更多人理解這世界到底是什麼回事。
Q﹕ 我大概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在片子裡面,在警察局裡面,有人被騙了,所以需要錢,然後大家都表現得非常的慷慨。我覺得當大家知道您在拍的時候,就像您所講的,是會影響被拍攝者。我就在知道您是怎樣保持客觀的?
A﹕ 一個一個 (問題) 來吧。從來就沒有一個絕對的客觀,就我剛才說,我的介入一定會對別人的行為產生影響,但是有時候這個行為影響,我也願意樂觀其成的。像我在警察局裡拍十天,那些警察不可能只照顧我的鏡頭,連續十天都給出好多好多的錢,這個是不可能的事嘛,另外在不記得是第一天或第二天,有個女警察就告訴我,她也快五十歲的人了,她在剛當警察的時候,有時候會給錢嘛。然後老警察就在旁邊看著,笑說我看你可以給多久。我也拍了一個片子是講急診室的故事,看的時候你可能覺得為什麼護士醫生特沒有人情味,但是你每天都要面對這樣的情況,其實人還是會產生變化。
Q﹕另外我也想知道更多您跟拍攝對象打交道的經驗。
A﹕我的經驗是第一時間你要跟人家說清楚你為什麼來拍。別人同意就沒問題了,別人不同意你就繼續去找願意被拍的對象。你看到都是我成功的案例嘛,其實人家拒絕我的時候是大多數的。我一直覺得,譬如說,我有一個拍攝的欲望,別人有一個被拍攝的欲望,必須要這兩個圓圈交集我才能做下去,就是要去尋找這個有交集的人,而這個情況起碼十之一二是有的。

Q﹕謝謝周導帶來一套這麼有深度的影片,讓我們能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中國的執法部門。在整部影片中,我有聽到三、四次有人提到救助站的問題,我想知道為什麼那些人去警察局,而不願意去救助站呢?還有您會不會想去拍一下廣州的救助站?
A﹕我當然會想去拍救助站,我覺得那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救助站就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部門,譬如說,你去了一個陌生的城市,錢被偷了怎麼辦?中國就是有這麼一個專門的機構,就叫救助站,任何人只要走進去,它也會給你提供適當的路費。中國是有這樣的機構的。在《差館》這部片子,就有一個非常有小聰明的貴州人民,他就把所有工資都寄回家,然後每年春節的時候他就會走進救助站說他沒錢,但春節到了,他要回家,他每年都通過這樣的方式回家的,這就是小人物的智慧呀。你是不是很難想像有這樣的人會用這樣的方式來跟社會打交道,這跟我拍派出所時的感受一樣,天呀,原來還有這樣的人。
他們不去救助站的原因就是救助站相對來說就是硬板床,但去派出所就想可以得到幫助,因為派出所會盡量幫他們解決問題。去了救助站就被視作一個羣體嘛,也不會得到特別的照顧。人都是出於利害的嘛,派出所能提供最大的利益,他們就去派出所了。
Q﹕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我有點小八卦,剛才片子裡的警察就不願在鏡頭前透露有關界線的問題,請問他最後有沒有跟你說拘捕與否的界線在哪裡?
A﹕大概就是一個原則,就是說,你第一次被抓到的話就會被警告,然後第二次被抓就要關十二個小時,這是中國的拘留法,再來第三、四次呢,就要把你關起來半個月左右的狀態。我覺得那個警察表達出來的態度,還有他跟我說話的方式就說明這種事情本身也沒有一條很明顯的界線,就是在模糊之間去執法。跟心情也很有關係。這法律的東西,哪有一個絕對的標準。你可能說一句客氣話就不會被抓呀,你要跟他硬碰就很自然會被抓。
Q﹕ 謝謝周導,我有一個很短的問題,在您拍攝的途中,有沒有哪些事是會讓你內心有些波瀾?
A﹕ 肯定有。拍紀錄片呢,如果拍完整個片子,其中沒有情節是讓你特別心動的,那我覺得就很難讓觀眾心動。譬如說,那個賣板凳的老人跟我說不要拍了,我的內心其實也是有一個小震動吧,就是我心裡會想我到底該怎麼處理。還有那個河南鳳陽的姑娘,她含著淚跟你說話的時候,你肯定也是會被動容的吧,因為就是特別生活的人嘛。這個世界,就是由警察、這些老人、女人共同組成的嘛,大家共同地在這個世界,然後看著他們你也會更深刻的了解這世界到底是什麼回事。我就是這麼的一個感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