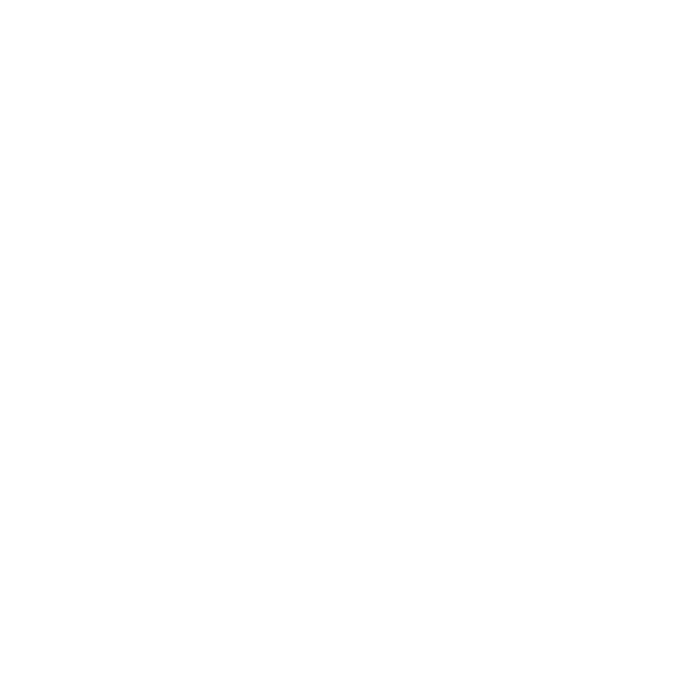【喜舊創新:紀錄片的創作與賞析】4月2日影評人映後座談節錄
4月的放映選片與【實驗電影】相關。選片包括《遺忘越南》、《莉維達.地海之詩》、《日月無光》,以及麥海珊導演的短片作品《再見》、《邊個驚鬼!?》、《火車過客》及《不是大藍天下的願望井》。這些紀錄片以非傳統敘述形式,由作者引領觀眾走進宛如散文、文本、詩集以及等,由影像與絮語交織的光影世界。
影評人安娜於4月2日向觀眾賞析《日月無光》,這是一部在法國新浪潮時期十分活躍的導演Chris Marker執導的電影作品。本片貫穿於一個女聲讀信的囈語當中,日本、冰島、畿內亞、香港各種影像交叉著,但是作者把最多的時間留給東京。他記錄日本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標誌性的招財貓、宗教儀式、性文化、漫畫、鐵道、珍珠港、搖滾樂、街上的舞蹈…..為觀眾呈現經濟奇跡後的日本最真實的一面。作者用影像寄託著他對人類現狀的關注,對歷史和記憶的思考。
安娜分享了他對《日月無光》的感想,並為觀眾介紹創作這部電影的導演Chris Marker的電影生涯。究竟Chris Marker經歷過的事物,對於他創作電影有何影響?他創作《日月無光》的時候,怎樣考慮剪接和攝影的方式,說出他想說的故事? 大家也可以看看這次分享。
安:大家在星期日下午過來看這部比較實驗性的紀錄片作品《日月無光》(Sans Soleil),香港中文名通常稱為《沒有太陽》比較多。看《日月無光》是非一般假日的選擇(笑)。為甚麼大家會來觀賞電影呢?看完之後,它是否符合你們心目中的期望?有沒有很大出入或者不同之處?或者有沒有觀眾完全不明白,看得一頭霧水?
觀眾1:我也是第一次看這部影片,感覺就好像在看《圖像策》,是另外一部電影。我覺得當中的內容很相似,其實好像都是以戰爭為主題,又有涉及一些關於人權和社會議題,令我覺得它很廣泛,總之就像一部包羅萬有的影片。該怎麼說呢……看到最後的時候,我覺得有點迷惘。
安:但是那種迷惘是不是正面的?
觀眾1:對,正面的。
安:所以你也會喜歡好像《圖像策》的類型嗎?
觀眾1:OK,我也會去看。
安:這個觀眾剛才說的《圖像策》,其實是尚盧高達導演在幾年前的錄像作品《圖像策》(The Image Book, 2019)。
觀眾2:首先,這部電影的名字很有趣,意思即是「Sun-less」。電影的最初有一個畫面,就是三個冰島小朋友,我以為他會以這些小朋友作為主線,帶出後來要講述的東西。不過並非如此,好像跳來跳去那樣。我很喜歡片中有一句說話,就是「如果你在畫面裡面看不見快樂,至少你也能夠看見黑暗。」我覺得這句說話很有啟發性。其實我也需要一些時間沉澱一下,反思它的前文後理,哪些內容是有關係。我看到今天有很多年輕人來看電影,也許你們很年輕,其實在這部電影裡,拍攝了當時日本經濟最繁盛時代的畫面。
安:你當時是不是很喜歡日本文化?有沒有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
觀眾2:沒有,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笨的人,當時不知道甚麼是文化。其實我覺得文化是跟自己的經濟情況相連,沒有金錢就不會接觸到這麼多東西,就算現在回看以前的時候,自己當時曾經在那個年代生活過,會覺得這些東西似乎跟我沒有關係。
安:我想向大家簡單介紹這部影片和導演Chris Marker的背景,還有我自己接觸本片的一些經驗。我在十多年前第一次看到這部電影,其實Chris Marker最出名有兩部作品,一部是本片,另一部就是《堤》(La Jetée, 1962),是一段長約30分鐘的黑白短片,形式就是基本上沒有動態影像,全部都是硬照。他透過硬照和旁白,講述一個具有科幻意味的故事。它很有趣,故事講述假想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變得蕭條,不適合人類居住。於是,地下軍訓練一個有特異功能的人可以回到過去,要去改變一些事情,令戰爭或人類毀滅不會出現。當男主角回到過去的時候,他不去做正經事,卻戀上了一個女子。加上,他自小開始就有一個畫面經常纏擾在他的腦海裡,那個畫面就是一個男人在機場死亡的情境。詳情我不想劇透了,它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又牽涉到跟《日月無光》有關的主題,包括記憶、忘記等。我們如何透過影像,去追憶或紀錄一些我們看見的東西,又或是用影像紀錄下來的東西有多真實呢?
我很喜歡《堤》,因為很容易明白之餘,更是一部很吸引的電影。Chris Marker本身是攝影師出身,所以他的攝影工夫非常好。但是,你們也許想到整部電影長約30分鐘,畫面是靜態,只有硬照,會否很沉悶?其實不會,它非常有趣。當時,我也想了解多一點這位導演的作品,於是看了《日月無光》,當時完全看不明白。我想補充一下,我們這天觀看的版本是法文版。其實在一些英語國家,會播放英文版。英文版也是由一把女聲讀出旁白,兩個版本的內容基本上很相近,但是感覺很不同。假設大家都懂得英文,當你聽到一把女聲說出一些你能夠立即明白、不用字幕輔助的對白時,看電影的經驗也會不一樣。我第一次看的時候,可能是看英文版。但是,這樣對於我去理解這部電影並沒有幫助。我當時只是覺得很辛苦,終於看完了。它長約100分鐘,但是好像看了300分鐘那樣,更不明白它究竟想說甚麼。這一次看完之後,我的腦海裡留下了很多影片的畫面,譬如一開始的三個冰島小姊妹、日本街道的風景,一些雀鳥、非洲人的面孔等,令人難以忘記的就是長頸鹿死亡的一幕。我會記得這些東西,但就不明白為甚麼會把它組合在一起,又會想到究竟片中的旁白想表達甚麼,說是「散文電影」,也會有一個主題吧。直至最近因為我要準備今次分享會,所以又再看一次,出現了一些很不一樣的新看法,因為距離我第一次看的時候已經有6至7年了。
我向大家介紹一下這部影片的製作背景。有沒有人認識導演Chris Marker,或者看過他的其他電影?有兩個觀眾舉手。也許大部分觀眾對他有點陌生。大家如果熟悉電影、知道歐洲電影的話,就會知道法國電影新浪潮,Chris Marker很多時候會歸類為新浪潮的其中一個重要成員,跟大家可能聽過的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伊力盧馬(Éric Rohmer)、積葵利維特(Jacques Rivette)、查布洛(Claude Henri Jean Chabrol)等人有點不同。剛才說的那些導演會被歸類為電影筆記派,因為這班導演是由影評人出身,在《電影筆記》雜誌撰寫影評,所以稱他們為電影筆記派。
另一班導演稱為左岸派,他們很多都有文學的背景。你會發覺在50年代的文藝圈的人,已經很活躍攝影、劇場、小說等,(他們)比較上有文藝氣息,或者是當時活躍的知識分子。成員包括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大家有沒有聽過《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 1959)、《去年在馬倫巴》(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 1961),都是他的作品。還有一個法國很出名的女導演艾麗絲華妲(Agnès Varda),通常會被歸入左岸派。至於另一個會被歸入這個派別的導演就是Chris Marker。如果跟其他新浪潮的成員比較的話,他的年紀較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甚至曾經參與過法國反抗軍。在大戰之後,他寫了很多小說和詩,更會攝影。由1950年代中期開始,他開始拍攝一些紀錄短片,尤其是他去不同地方旅行的時候拍攝了一些影片,然後把它剪輯成一些紀錄片。他拍過甚麼?其實他拍攝過中國,有一部《北京的星期天》(Dimanche à Pekin, 1956),片長大約20分鐘左右,有很多音樂配襯,拍攝50年代的老北京。它是彩色電影,色彩非常斑斕。Chris Marker拍攝了當時北京平民在里巷之間的生活、好像練習體操、玩剪紙。他亦到過西伯利亞和古巴旅行,拍攝了一些紀錄短片。
在60年代,除了我剛才提及過的短片《堤》之外,Chris Marker拍攝過一部很重要的紀錄片《快樂的五月》(Le Joli Mai, 1962),他當時用一些比較新的方法,或者說是直接地跟一些被拍攝的對象交談、訪問,譬如一起討論關於巴黎的東西,甚至很多人生問題,之後剪輯成影片。他的拍攝方法未必很被動,拍攝一個人,然後一問一答。有時候,他們會更加願意,主動跟被拍攝對象進行交流,甚至會說一些質疑對方的說話。當時Chris Marker拍攝了《快樂的五月》,另一部法國紀錄片就在差不多時間出現,《夏日紀事》(Chronicle of a Summer, 1960)被視為一個比較新式的拍攝紀錄片的方法。他們當時有一個名稱是「真實電影」(Cinema verite), verite的意思是真實。有些評論人認為這種特別的紀錄片方式,即是拍攝者願意直接介入,與被攝者溝通,會是一個更加能夠貼近真實、得到某些真實的方法。(1424)《夏日紀事》的導演(Jean Rouch及Edgar Morin)是有人類學的背景,所以他們對於紀錄的方法,還有如何透過溝通、用文字紀錄下來的方法來得到一些真實資訊,都會比較在意。不過,Chris Marker對於這些東西並不太有興趣,甚至抗拒這些標籤。有一個說法是,有人用「Cinema verite」來形容他,但是他把這個詞語改為「Cine, ma verite」,意思是「電影是我的真實」。他拒絕紀錄一個所謂客觀的真實。所以在《日月無光》裡,可以看到Chris Marker很強的個人色彩。
至於拍攝這部影片之前,他在60至70年代幹甚麼?他又怎樣過生活呢?其實那段時期是他比較左傾的時期。他嘗試透過很多主動介入的方法,希望用影像來推動或者幫助一些抗爭運動。他其中一個比較早進行的試驗就是當時有一部影片《遠離越南》(Loin du Vietnam, 1967),一班新浪潮導演以及其他派系的法國導演,共同拍攝了一些以越戰為主題的雜錦影片。除了聲援反越戰示威之外,同時希望更多人關注越戰的事情,Chris Marker亦有參與其中。拍攝完《遠離越南》之後,他曾經有一段時間和工人階層很接近,又參與過一些工人組織,並拍攝一些關於工人運動和工人權益的影片。他希望透過影像,能夠幫助到法國以至其他地方的工人及無產階級,左翼正是推動一些他們想去爭取的東西。到了1970年代中後期,當全世界,無論歐洲還是亞洲,一時之間就有了很火熱的左傾思潮,一些抵抗、反體制的運動開始退卻,甚至是有很大的變質,《日月無光》也有提及到,當時日本軍隊變成了一種紅色的恐怖主義,互相撕殺、殘殺,甚至權鬥。Chris Marker在70年代的中後期,開始遠離了希望透過影像介入政治和社會運動的行動式做法。
《日月無光》是1983年的電影作品。很多時候,它會被視為Chris Marker第一部回歸個人電影創作的相當重要的作品。裡面絕大部分看得見的畫面都是他自己拍攝,他在1970年代到過很多地方,譬如日本、位於西非的畿內亞拍攝。
影片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形式,大家第一次看的時候可能未必發覺到,它其實用了書信的形式,來講述和組織影片的旁白。在片尾可以看到,原來這些信件是由一個名叫Sandor Krasna的人撰寫的。他究竟是甚麼人?那一把讀旁白的女聲會經常說「他寫著:……」、「他說:……」,這個「他」可能就是Sandor Krasna。他可能是一個攝影師,曾經到過不同的地方,拍攝一些影片裡面看到的畫面,然後寫下一封信,再給那個讀旁白的女人讀出來。然而,現實中並沒有這個人。這個「他」是Chris Marker的化名,而且信裡面的文字都是他自己寫出來,影片也是他自己拍攝。這個電影導演將自己的身份和重要性降低,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好像是他自己創造了一個虛構的人物,並說那些信是「他」寫的。
另外,很多人也會提到一個重點,這部影片從來沒有提及誰是導演,畫面也沒有列出導演姓甚名誰,只是在最後有一行字「Conception and Editing by Chris Marker」。有些人會這樣演繹,因為他在60、70年代參與了很多集體性以及左翼的創作,所以遺留下來的影響。他當時參與創作的時候,通常是以不具名的方式參與,而這個形式也延續到《日月無光》,它只是由Chris Marker構思出來,好像他並不是真正的導演,但事實並非如此。
我會形容今次看《日月無光》是一個很奇妙和神秘的體驗,彷彿進入了那個人的腦海裡面。有一類電影名叫「Essay Film」,即是散文電影。《日月無光》在散文電影的發展當中,可以說是一個相當關鍵的里程碑。由這部電影開始,之後出現了一些比較可以自由剪接影像,或者加上不同旁白的電影。雖然裡面好像一篇散文,但是一篇散文也會有主旨和題目,但是這部電影沒有主旨,甚麼都可以說,由最所謂無謂的廣告牌、電視正在播放甚麼東西、似乎是隨機聽到香港電台的廣播,當時可能是某一年的農曆新年,好像聽到是狗年的年初一。其實這樣不是很重要,也沒有值得驚訝的地方。又或者在一些很重大的命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記憶、又或者是科技等,這部電影都有包含在內。我感覺到它的剪接或者思路的進程,真的好像一個人正在思考那般,當你沒事幹、把腦袋放空的時候,你由一個念頭開始,然後會想到一些東西。有時候,人的思路並不是這麼直接,即是首先會完整地思考事物A、然後才到事物B。反而,人的思路有時候是會跳躍的,想起事件A當中的某件事,然後會聯想事物B;事物B也可能會令人回想到自己曾經想過,但就仍未處理的事物C,突然之間在那一刻想通了事物C,有了一些想法之後,最後才回去再想事物A。我覺得這部電影也有一種這樣的特質。它的剪接和進展是在擬仿一個人的思路、思考的過程和方法,所以我覺得它很有趣。
剛才有觀眾朋友提及到,影片一開始有一段關於黑暗和沒有太陽的那句旁白,我也想向大家分享一下。當我準備這次分享會要說甚麼的時候,我也翻看了這一句旁白很多次。我覺得影片這樣開始很有型,大家還記得在《日月無光》片名出現之前,一開始是怎樣呢? 它只有兩個影像,第一個是拍攝三個冰島小女孩;第二個則是拍攝一部戰機正在一艘航空母艦的甲板上降落。
至於女聲旁白就是這樣說:「他告訴我,第一個畫面是在1965年拍攝,冰島的一條路上面有三個小女孩。他覺得這個畫面代表快樂。然後他試了幾次,把這個畫面跟其他畫面接合起來,但是不太成功。他寫著:『我會把這個畫面單獨放在影片開頭,和一段很長的黑畫面接合在一起,如果觀眾在影片裡看不見快樂,至少也會能夠看見黑暗』。」
我覺得,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分鐘,但我覺得這個影像試驗十分有趣。第一,這兩個畫面本身沒有特別意義,裡面也沒有故事,或者稱不上是任何形式的「奇觀」。不要說它是平庸的影像,這兩段畫面都是一些很普通、尋常,而且一向會見到的影像。不過,當你把它們接合在一起的時候,對於我自己來說,我會有一種很奇異的感覺。怎麼會有可能呢,冰島的一個草地上,有三個看起來很開心的女孩子,又怎樣跟一個象徵權力和暴力的戰機畫面接合在一起?這樣很不合理吧,在邏輯上,兩種事物根本沒有直接的關連。但是在影像上,我覺得把兩個畫面接合在一起,就會有一種震撼力。而這種震撼力,會早於解釋之前,或者是早於理性思考或者理解導演為甚麼會這樣剪接之前。我覺得這個剪接方式的影像,本身就已經很有力量。
第二就是關於黑暗。我不知道旁白是怎樣寫出來,不過有一個東西就是,黑暗和快樂的關係是甚麼?它們的分別是甚麼?快樂是一個主觀的感覺。究竟多少人會在三個女孩子的影像裡看見幸福或者快樂?沒有人可以肯定,甚至導演也不能肯定戲院裡面,究竟有多少人會看見幸福。因為它是主觀的演繹,究竟那個畫面能否代表幸福?但是,黑暗並不是這樣。黑暗是絕對的,如果把一個黑畫面放在影片中,觀眾就會看見一個黑畫面,並不是指憂傷、死亡或悲哀。黑就是黑。黑暗和快樂這兩種東西,一個是很主觀,未必有一個絕對的標準以及需要演繹的性質。另一個是很確切、很確定的東西。我覺得整部紀錄片就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搖擺。我們看到很多確切和真實的影像,好像招財貓、廣告牌、雀鳥,一部將影像合成和調節的機器,諸如此類。但是我們感受到的東西,每個人都不同。究竟我們會看見幸福,還是會看見其他東西?對於這些影像,Chris Marker全部都有很精細和細緻的感受,或者他想表達一些想法,不過並不一定能夠成功傳達給觀眾,更不一定可以說得出是甚麼,或者很具體地把它分辨出來。我覺得整部紀錄片就是在很絕對、很確定,而且又在客觀和主觀需要演繹的這些光譜之間搖擺、來回。
在這部影片裡面,很多影像都是他在旅行期間拍攝,譬如他去過日本和非洲旅行。我覺得這部影片很好看或者令人思考的地方在於,它並不是直接地描述畫面,而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特別是你會覺得好像敍事者去完旅行之後,一年之後再次翻看這些畫面,這時候才有一些感悟的那種感覺。尤其是在非洲拍攝的那一段,那個「他」特別提及到,畫面上那兩個受勳的少校和士兵一年之後就會奪權,並會把當時在任的總統路易斯卡布拉囚禁起來。「他」就說,有時候要用一種超前現在的眼光看待事物,才可以看得見事情的真相。由於有了跟這些東西很類似,又超脫於事情本身看法的角度,我覺得這部紀錄片跟其他散文電影很不一樣。
好像觀眾提及過的《圖像策》,或者尚盧高達的其他電影作品,我覺得這位導演有一些可以跟Chris Marker比較的特點。尚盧高達由大約70年代起已經拍攝很多非劇情、靠近紀錄片形式,但就含有大量闡述式內容的電影。除了《圖像策》之外,他最重要的電影作品包括了電影史,或者他早期拍攝了一個近似散文電影類型的作品《給珍的信》(A Letter to Jane, 1972)。如果大家把這部電影跟《日月無光》比較之下也會很有趣。《給珍的信》的Jane是荷里活女明星珍芳達(Jane Seymour Fonda),她是一個很熱心支持反越戰運動的名人,甚至運用自己的號召力和名氣出席大小場合,希望大眾可以了解和支持反戰的立場。珍芳達甚至因為覺得跟尚盧高達的政治理念相同,大家都是支持反戰的立場,所以幫助他拍攝一部電影《一切安好》(Tout Va Bien, 1972),就是講述左傾和反資本主義的政治理念。高達拍攝這部52分鐘的散文電影《給珍的信》其實是批評珍芳達身為荷里活著名影星,卻去支持反戰,又說自己體恤越南人民,這樣做是偽善和虛偽,也覺得她本身屬於資產階級之類。《給珍的信》特別之處在於,這部電影的畫面有近八成是一張照片,就是珍芳達稍為彎下身聽一些越南人說話,然後高達用一些相當教條式的語言,透過圖像來解釋一些符號化的東西,即是把照片變成符號來解讀,批評珍芳達的立場和為人之類。高達的這部電影有一個很值得比較的重點,就是除了有一個明確立場之外,更有一個要明確闡述母題的中心。就好像老師教大家寫作的時候,首先要為文章設定一個主旨,其次每一段都有段落大意,然後怎樣敍述文章重心,或者在每個段落之間拓展或推展論述,最後會成為一篇結構完整的文章。高達的電影基本上就是這樣。若大家有機會看高達的其他電影作品,其實會很強烈地感受到這個人有很多話要說,有些東西是他想灌輸給你;有些東西是他認為是正確的,所以有點強迫,用一個近乎權威的姿態,把一些道理、看法和分析告訴觀眾。不過,Chris Marker的《日月無光》並不是這樣,我會形容他的方式比較上令人覺得舒服,原因是他不會介意觀眾跟不上一些旁白和內容,事實上真的一定會跟不上,因為太快了。今次放映是法文版本,無論法文的旁白也好、加了中文字幕也好,坦白說,這部紀錄片講述的東西並不是言語對白,更不是閒話家常,而是一些很深奧的東西。片中經常會引經據典,有時候,你也不知道它在說些甚麼「禁區」,其實引用了塔可夫斯基的《潛行者》(Stalker, 1979)。若你不知道塔可夫斯基或者《潛行者》的話,你可能就會感到迷失。
導演利用那個影像合成器,將影片轉化成一幅幅色彩斑斕的圖像,就像玩耍那樣,令我看得樂在其中。我覺得那種抽象化、顏色的轉換,本身都是一些可以欣賞的東西。譬如本片中段有一個部分提到日本的神風突擊隊,導演選擇把那些影像全部都不用真實的色彩呈現,反而用了影像合成器來過濾它,然後才呈現出來。導演為甚麼要這樣做?大家也會有自己的演繹,會否因為暴力而有所調節?用影像合成器來調校影像顏色,是不是好像人的記憶會扭曲那樣?譬如片中引述了其中一個神風突擊隊隊員的說話和證詞,其實跟一向人們對於他們的印象並不一樣。片中引述了一個神風突擊隊隊員上原良司的說話,他說自己在飛機上就像一個金屬製造、沒有感情的機械人,但是在陸地上,他曾經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他認為自己的國家若要得到解放,就要得到思想的自由。其實他們並不是想像中沒頭沒腦、只會完全服從國家或服從命令的軍人,他們跟大眾的想像有點不同,導演用影像合成器扭曲或者改變影像顏色的行為,是不是跟這樣有關係?我覺得其實也可以有這樣的演繹。
最後,我補充一下。我覺得《日月無光》有一個最大的啟發,也是呼應我最初說過的東西。很多時候,當我們看電影,或是從事影像創作的人經常想去拍攝一些驚天動地的東西,又或者如何拍攝才會令畫面好看、令它更有意義等等。尤其在現時拍攝器材那麼方便,就連手機都可以拍攝,只要你想去做的話,看見一些值得拍的東西時,也可以立即拍攝下來。更甚是,我們每天瀏覽instagram上的帖文和限時動態,每個人其實也不自覺地拍攝了很多短片。但是這樣又會迎來一個更大的問題,既然是拍攝電影,即是去拍攝自己的作品,影片裡也可能一定要有些很厲害、很有意思的畫面。不過,Chris Marker告訴你並不一定要這樣做。當你選擇拍攝一些畫面的時候,也要經過自己的眼睛篩選。他是一個很優秀的攝影師,影片中的畫面構圖都是十分精巧。有時候,電影的感人之處和力量未必只是在畫面上,反而在畫面與畫面之間,或者在畫面與聲音之間。就好像影片一開始的時候,觀眾可能都會有很深印象。如果我只把三個冰島少女的影像給你們看的話,你們不會有很大的感覺,覺得只是三個笑容可掬的青春少艾。但是,導演透過一個很突兀的剪接,把戰機畫面、黑畫面與前者接合起來,再用旁白把它框住之後,就變成另外一種東西。導演很多拍攝日本的畫面都是一些街頭即興、類近Snapshot式的紀錄,拍攝了一些橋、火車及路過的行人。這些畫面並不是拍攝一些很重要的時代大事,又不是拍到某個政治人物被暗殺,更不是拍攝關於新年和一些特別節慶的畫面,本片裡面的畫面都是圍繞日常生活。透過這些影像,導演能夠反思到文化底蘊,又會從旁觀者的角度嘗試了解。但是,他永遠都看不見核心,去知道日本文化,然後反思一下自己作為一個沒有根、沒有家的旅行者的心態及境況。
我記得另一個法國導演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曾經說過評價Chris Marker的說話。他覺得Chris Marker真真正正是一個21世紀的人,他比所有人走得更前。當時,電子產品和錄像產品只是剛剛面世,並開始流行的時候,Chris Marker想到了錄影帶以及無窮無盡的影像,本身都可以建構出一個世界,或者改變我們對於過去與記憶的某一種思考。《日月無光》於1983年拍攝,今年剛好踏入40年,我覺得無論內容、對於世界或者影像本身的思考,以至影像本身、聲畫配合本身,不但從未過時,就算在十年後再看一次,影片仍可超越前人、有一種很新鮮的感受,甚至各位之後有機會再看的話,可能也會被這部電影震撼到,看到更多、更新的東西。其實很難用一句話概括《日月無光》的內容和主旨是甚麼,若大家有任何得著,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帶著一些影像,以及一些曾經觸動你、一些令你在腦海裡面留下深刻印象,不停迴響的句子回去,然後有一天重看這部紀錄片,也會可能改變你對於這個世界的看法,譬如看一些影像、或者看身邊事物的看法。
觀眾1:我第一次看這部電影。它看似很隨意,就像隨想地把一些影片拼湊在一起。影片的前段有點令人想睡覺,加上字幕轉得很快,有時候我還未消化到上一句,就已經出現下一句字幕,因此未知道它想說甚麼。然而,有一些片段會在影片裡面再次出現,譬如日本人在祭祀時把玩偶燒燬的儀式 ,中國人也會做一些類似的法事,好像我們會在孟蘭節的祭祀活動把大士王燒掉。影片裡面不斷重覆一些鏡頭,令我漸漸想起有一點關連的意味。好像一個旁觀者那般,看著一種文化,即使他不明白有甚麼意義,但就好像在思考一些東西。我作為觀眾,就會套用自己的文化背景,思考一下影片帶給我們的意象以及意思是甚麼?另外,影片最尾部分有一個香港電車的鏡頭,令我突然想起很多自己身處在香港環境的感覺。我覺得看整部紀錄片的時候,我會以片段式的方法進行思考和反思,未必可以確實地講述具體的內容,不過隱約地是有一些東西貫穿全片,但是不太確定究竟是甚麼。鏡頭的對比是會令人覺得有力量存在。
安:謝謝,我再補充一下。我想到一個很特別的東西。法國人是其中一個最喜愛日本的民族。法國人對於那裡的印象,就是由十八世紀的一些浮世繪版畫而來,當那些畫作傳入法國之後,法國人對於日本有了很多幻想與好奇,而且從未停止。Chris Marker在70至80年代到日本旅行,當時的日本繁榮興盛,而且發展迅速。我想他對當時看見的所有東西,都會覺得很新鮮,又新奇。法國社會學家羅蘭巴特有一本著作《符號帝國》,就是由不同角度敍述日本,在這個遠東國家裡,也會跟法國人的生活一樣,都是有衣食住行,但是日本人的做法就是透過一些符號和樣式來進行。譬如日本人的衣著、談吐、習俗,還有一些規範,我想這些東西對於法國人來說,是一種很新鮮的刺激。那怕是一座電話亭、火車軌,一些正在通勤上班的人,或者一些在公園聚集的人,他們都拍攝得津津有味,就像到了一個外太空星球般興奮。大家有沒有感受到導演拍攝日本的時候,那個部分很好看,但就覺得畫面給我的感覺就是好像人類到了一個外太空星球那般,或者好像一個小孩到了一個全新的地方,覺得所有東西都很新奇、美麗和好玩,我覺得導演拍攝的鏡頭有這樣的感覺。
剛才觀眾提及到香港,影片很快地加插了幾個電車的影像,又聽到電台的廣播。我有一種感覺,它是一部很前衛的電影,就是講述世界彷彿沒有了距離,只要打開手機,然後開啟通訊程式,就可以立即知道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正在發生甚麼事情,無論畫面還是聲音都可以立即傳達,讓我們可以看到。然而,在50年前未必可以這樣做,因為當時沒有這些東西。時至今天,我們對於距離和地域的想像已經徹底改變,我覺得當時拍攝《日月無光》的時候,這個東西未必很明顯,或者處於一個正在改變的階段。在這部紀錄片裡,由一個非洲的角落小島、沙漠、燈塔,然後聯想到在香港暫居和過境的經驗。那些在眼前閃過的畫面,就像一個幻象那般。我覺得這樣的感覺很棒。(觀眾哈哈大笑)
坦白說,我覺得這部電影很難評論,難處就是很難闡述,還有找出一些有意思的東西。大家還記得最後的那個畫面是甚麼?就是有一隻手拔起了影像合成器的針,當拔起了那支針之後,後面有一排射燈由背景方向照過來,接著就是黑畫面。它們其實沒有特別意思,但我覺得它非常有型。這是一種節奏,當你不斷地看一些連續的畫面,畫面本身沒有剪接,也沒有一個很大的鏡頭運動,只有比較緩慢的顏色轉變,然而拔起了那支針之後,就有很強烈的燈光射到鏡頭前面,sharp cut之後轉為黑畫面。無論如何這就是影像的力量,幾乎沒有辦法轉譯出來。
觀眾2:我覺得今天看的《日月無光》是一部很需要聚精會神來觀賞的電影。雖然我今天並不是很集中精神,但是它令我很意外,當中有很多影像都為我帶來衝擊,有些說話也很令人感動。我覺得有一幕十分有趣,導演拍攝在日本一輛電車上睡覺的乘客,我覺得拍得很美,而且把每一個面孔都放得很大,很清晰。然後就混雜了一些鬼怪恐怖電影的影像,好像把那些人引入一個聯想,例如他們在發些甚麼夢,他們有甚麼感覺之類。之後就不斷重覆這些面孔的影像,後來更用了影像合成器把它轉成很多顏色。有沒有特別的解讀?或者你會聯想到甚麼?
安:我覺得這一段能夠展現出創作者Chris Marker有一種在影像上的幽默感。首先是那些乘客的面孔影像,會跟一些恐怖電影裡鬼怪面孔特寫的影像接合在一起,你會覺得這兩種影像好像有點相似,而且還是比喻這些睡著了的人。畫面上千奇八怪的面孔,就好像那些鬼怪。另外,我記得還有一段加入了動作的畫面,好像在說畫面裡的那個人可能正在思考、又或者正在睡夢之中。然而,由於這是剪接出來,所以並不會確實知道那個人夢見甚麼。
其實那些影像都是在一些電視劇集擷取下來的畫面,跟那些在電車上睡覺的人完全沒有關係。我們一方面可以在影片裡看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看似既沉悶又平庸;另一方面,當時的日本十分流行看電視,那些節目的影像可以說是鋪天蓋地,到處都是很流行。導演用這種方式將兩種影像接合在一起,令我覺得很有趣。因為電視上的那些畫面代表娛樂性、消費,亦是人們不會特別重視,更是一些沒有價值、很輕的東西。當我們把這兩種事物用剪接方式拼接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那種反差很有趣。基本上,沒有人想過可以將這兩種東西用剪接方式拼合起來,我覺得影像的幽默感很突出,能夠展現出Chris Marker的特色。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看Chris Marker的電影作品,便會知道他充滿幽默感。我很喜歡貓,大家也可以看看,其實他在1988年拍攝了一段短片《貓咪聽音樂》(Chat écoutant la musique),內容是有一隻慵懶的貓正在鋼琴上睡覺,牠突然之間醒了,又走來走去,全片配上一段鋼琴音樂。他透過不同的剪接方法,或者好像《日月無光》那樣,用影像合成器來調校影像。他拍攝了這部很短的錄像作品,好看之餘,而且很有幽默感,突顯了他在電影生涯的中後期,有了一個很大的作者特色。
謝謝大家,謝謝CNEX的邀請。
安娜為4月份選片撰寫的影評已經刊載於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網站(按此)。
https://www.filmcritics.org.hk/zh-hant/node/3151
簡介:
安娜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理事會秘書,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及香港演藝學院電影及電視學院兼職講師,電影創作團體「豐美股肥」創辦人之一。編有《香港電影2021:世界是你們的還是我們的》,編導短片包括《一Pair囡》、《鵲橋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