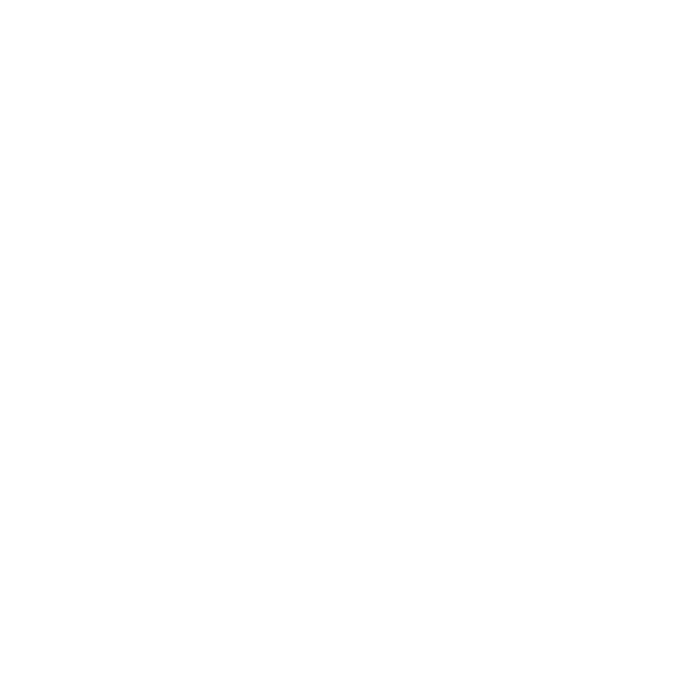【喜舊創新:紀錄片的創作與賞析】3月25日導演映後座談節錄
【喜舊創新:紀錄片的創作與賞析】3月份放映五部影片《我們在黑夜的海上》、《為我哼首搖籃曲》、《四次旅行》、《念你如你在》及《日常對話》。導演把鏡頭面向自己,透過影片向觀眾展示自身經歷及故事。
《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於3月25日出席映後座談,由潘達培先生擔任對談人及分享會主持。黃惠偵導演向觀眾剖白她拍攝這一部關於個人和家庭生活紀錄片的過程,與此同時,也修補了她和媽媽之間的關係,化解了雙方在溝通方面的困難。她現在已經放下心裡面的鬱結,跟家人一起快樂地生活,更正在製作她的第二部長片。黃導演說話很幽默和有趣,令大家哈哈大笑。
黃惠偵:黃;潘達培:潘; 現場觀眾:觀眾
潘:我覺得很難得,因為你要把自己也拍進去,更是拍攝關於自己的事情。你在甚麼時候決定要跟媽媽溝通,而且要用拍片的方法去展開,為甚麼你會選擇用紀錄片呢?
黃:香港的觀眾大家好,聽說這天天氣不太好,謝謝你們在這種下大雨的天氣情況之下,也過來看影片,真的很感謝各位。
其實從我20歲那一年已經想去拍攝,而且也真的開始了。只是我當時並沒有跟我的母親講得非常清楚,自己到底在幹甚麼。因為這對於我的媽媽來說,這樣做有一點干擾…以及是,我的媽媽是一個連電影院也不會進的人,她很難想像和理解一個拍電影跟拍紀錄片是甚麼意思。所以,當時對她來說,她會覺得我當時正在拍攝Home Video,因為我的確在拍攝Home Video。家裡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會把它們紀錄下來。所以,媽媽一直以這種好像在拍攝Home Video的形式,這部紀錄片由我20歲那一年開始拍攝。我現在已經35歲了。到了很後期,我才認真地想去尋求電影製作資金,然後要找一些專業的製作人跟我工作,因為在那之前,我一直都是一個人去拍攝。
我在想,拍攝這種所謂的「私電影」,就是家庭故事的影像,好像比較容易觸動人的地方就是因為人們很多時候都是在「田野」裡頭,每天一拿起攝影機就能夠拍攝。可是,我覺得這樣也是它很難的地方,因為你太習慣自己每天身處的那道牆,你會覺得每天日復日都是一樣,如果你沒有一個很清楚、想要講的東西的話。所以到了後來,因為我找到了電影資金和專業的合作夥伴之後,我才比較正式地跟媽媽坐下來跟她說,其實在這十多年以來,我都是在拍電影,雖然你可能感覺不到,但我的心裡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是在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自己可能有幾個運氣很好的地方。當我跟媽媽正式提出想拍攝她的故事、她跟我們家的故事的時候,那個時間點剛好是落在2014年。那時候,台灣立法院正在修法要去爭取同志婚姻合法化。所以,外在社會有些事情正在發生,跟她自己的身份也有一些關係。因此,我覺得媽媽好像比較容易能夠理解為何我們家的故事需要被看見,我過去跟她提及過 ,但我覺得她真的沒有放在心上。其實到了2014年 ,我向她提及這件事的時候,她的回答還是說「我們家的故事有甚麼好講呢」。對她來說,我們家經歷過的這些事情都是不光彩的。我們華人很奇怪,就是家醜不可外揚,這是家醜,她會覺得這些事情有甚麼好說,到底有誰想去知道呢?但我覺得運氣很好的是,媽媽並沒有因為這樣而拒絕,因為我覺得自己當時是有思考過說服她參與製作的策略,就是我首先是動之以情。
在2014年的時候,剛好我的女兒已經兩歲了,媽媽一直跟我們一起住,直到現在也是。我覺得自從我的女兒出生之後,媽媽每天都會跟女兒一起相處。我覺得隨著她自己的年紀日漸增長,又會每天跟外孫女相處,家裡有一個新生命的誕生,這件事其實會為家庭的氣氛帶來一些改變。我在那個時候向她提出,想把我們家的故事紀錄下來,因為我比較晚生小孩,她當時也已經快要60歲了,至於我也30多歲了。如果以後女兒長大了、我們不在了,她也會知道我們家的故事,她亦會知道自己有一個很特別、跟其他人不一樣的外婆。當時,我的媽媽聽完這個第一個理由之後,她就點點頭,但就沒有說好還是不好。我接著跟她說第二個理由,就是剛才提及到,當時台灣社會正在討論同志婚姻合法化的議題。其實每一天都會看到很多新聞,譬如突然有一群人站出來反對同志擁有婚姻的權利,因此我跟她說在那個時刻,我們的故事講出來的話,就會特別有意義。我覺得這不只是對於我們家而已。媽媽聽完第二個理由之後,沒有拒絕我,就說「好呀,你就拍吧」。我覺得,她大概真的沒有很清楚地看看拍攝紀錄片到底是一個怎樣的過程,她的想像是好像覺得拍幾場就結束了,因為我跟媽媽進行過很多次訪問,她在每次訪問也會說「不是已經拍過了,為甚麼還要拍呢」,因此我覺得她當初並沒有以為會拍攝這麼長時間,但是總之她就答應了,我覺得真的在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之下,我向她提出這個邀請。假設再次找她拍攝十年、五年的話,我覺得那個狀況可能會很不一樣。如果我沒有生小孩、台灣社會當時也沒有因為立法而引起一些討論的話,那些狀況都是因為在特殊的時空底下,我覺得媽媽才願意答應一起參與這部影片的拍攝。
潘:是的。可是除了家庭故事之外,而且拍紀錄片有一個狀況就是會越挖越深,挖到了一個點就會是極限,尤其是一些關於個人私隱的東西。而且你更是紀錄片的導演,你在拍攝期間,有沒有經歷過這一種情況?尤其是我看到拍攝你與媽媽之間的對話的那一場,因為它是一個挖得很深的對話,你是怎樣處理這個難題呢?
黃:那一場對談其實是我整個拍攝歷程當中的最後一場。我很清楚這場對話不管是對於這部電影,還是對於我自己的生命來說,都是很重要,它一輩子只會發生這麼一次。如果我之後再跟媽媽談第二次,也不一定跟我第一次聊天的時候會是一樣。所以,我們會知道這是第一次談及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務。到底要聊些甚麼、在甚麼時候、用甚麼形式跟她談,我都想了很久。所以,不管整體性思考,或是比較我自己在感性上面的需求,我也想了很久,才決定把它放到最後。因為作為拍攝影片的人你會很理性,心裡面會告訴你,如果這場戲搞砸了,大概之後也不用拍了,所以並不適合在一開始就處理它。另外就是,其實要進行這場對話,我覺得自己也需要作出非常大的準備,還有要拿出我所有的勇氣,才有辦法進行。正因如此,那個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在一個關鍵點上,使我下定決心要去拍攝。
其實在拍攝期間,我的運氣很好,因為我有一個很好的工作夥伴,譬如我的妹妹、我的攝影師都對我很好,攝影師會告訴我,他覺得電影並不是這麼偉大,我們的生命和人生才是最重要的。今天不管我有否進行這場對話的拍攝也好,又或是我們拍了之後,最後決定不使用它也好,他(攝影師)作為一個主創團隊,會覺得都沒關係,其實他陪我拍了一年密切的拍攝之後,最後選的是這個給大家看到的片段,他也覺得OK。原因是,他的認知會覺得在陪伴我去完成生命裡一些很重要的事,不是只是在接一個項目、完成一個影片。我覺得這樣其實會是一個很大的支持,因為攝影師會把意見告訴我,我也會更深刻去思考,所以這一場對話,以及要不要把它原原本本地公開,那個意義到底在哪裡。我思考的已經不只是我自己,是因為我在年輕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曾經在台灣從事過社會運動的工作。我覺得也是因為那時候工作了這麼多年的時間裡,令我去思考、也去談論到在我們家裡發生性侵犯的經驗,我其實在想,這已經不只是我自己,為何這麼多年過去了,其實也很難去談論這件事情,因為我的父親後來自殺過世了,這件事情好像是……你最害怕的那個人已經不在了。可是,因為我覺得他對於我的影響非常大,然後真正的壓力好像已經不只是來自父親這個人,而是整個社會如何看待我曾經有過一個被性侵的經歷,或者是媽媽遭遇到家暴。反而一直到我去拍攝媽媽的時候,她還是覺得遭遇家暴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我就覺得自己很清楚這件事情是需要被拿出來以及公開討論,原因是我們之所以這麼痛苦,是因為這個社會一直讓我覺得,我們不應討論這些事情,講出來是很羞恥、很丟臉,而這些東西都令我很希望去改變它。
另一個很關鍵的原因是,我一直都很擔心。我跟媽媽之前就已經想對話,把這件事告訴她的話,好像特別會覺得我在責怪她。可是對我來說,我後來決定要跟她說這件事的理由, 完全不是要責怪她,而是我希望她找到一個能夠與之共處、 然後把它放下來的方式。我比我的媽媽幸福很多,因為我之前曾經參與社運,會用比較多不同的方法來理解在自己生命發生的事情。可是,我的媽媽並沒有的。像我媽媽這個年紀、這個世代的人,又沒有受到太多的教育背景,然後她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社會的主流價值如何看待這些事情,而她就是接收到這個所謂的價值觀。她一直都不敢去碰,也不敢去提。可是我覺得我比幸運很多,我知道問題不是在……其實,我不會說問題是出在我的父親,或是母親沒有擔當保護子女的責任,我都不覺得是這樣。所以,我會很希望她也能夠理解這一點,因為作為一個母親,我覺得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如果孩子有天受了傷,即便只是生病,你都會有非常強烈的自責和歉疚感。我覺得過去是沒有辦法去跟媽媽說,叫她把這些東西放下,其實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會很怨懟她,因為這是作為一個母親應該要做的事情。但在後來,我自己也成為母親了,我第一次意識到母親是有一種天生的……即使你不想要,也會感受到的那一種責任感的時候,我突然覺得我的母親很辛苦。只是,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去承擔這十多二十年以來,她一直不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可是的確地,事情也真的發生了,當年我跟我的父親一起過夜睡覺的晚上,是有發生事情。我覺得「不清楚」、「不明白」其實是更加恐怖。所以,我就覺得自己選擇去告訴她的這一場對話,是希望她知道在當年發生了這件事情,而且我現在已經能夠跟這些事情共處。它沒有傷害我、沒有打擾我……它曾經傷害過我,可是我已經找到方法與它共處,加上我已經跨過去了,希望媽媽也可以。如果我們兩個都可以跨過去的話,我覺得母女關係才有可能有所改變。因為我們的梳理,我覺得不只因為她作為一個同志、也不想要小孩,可是因為我一直有一隻不能夠去控訴和談論的「房間裡頭的大象」,你和我都知道,卻不可以談及的事情,才讓我們的關係變得非常疏遠。其實我很感謝電影,以及我十多年以來的生育經驗,讓自己可以用一個不一樣的角度思考這件事情,然後把它付諸實行。
潘:我也覺得不簡單,因為我在2016年看的時候,感覺很震撼,隔了這麼多年之後再看一次,都是覺得震撼。你的媽媽第一次看是在甚麼時候?她的反應是怎樣的?
黃:她第一次看的時候就是在2016年的金馬影展,那麼我就帶她去,我們整個家族都有到電影院去看《日常對話》,所以我的媽媽就是走進了她一輩子通常不會進去的電影院。那裡有一群金馬影展的觀眾,都是文藝青年和中年,我到現在仍然很感謝跟我們一起看首映的這些觀眾朋友,因為我覺得有一些事情就是,不管是這部電影,還是我跟媽媽關係的改變,觀眾其實幫我完成了我自己沒有辦法做到的部分。
那個時候,我記得放映完結之後,會有一些映後評委的環節,很多觀眾都舉手發言。他們不見得每個人都會提,可是很多人都一定會提到很感謝我們分享這個故事。原因是他們可能也有類似的經驗,不管是家暴、有一些家人是同志,甚至有些觀眾是同志,因為這樣的緣故,令他們跟母親和家庭的關係很不好,另外還有提到性侵犯等。可能很多人都會有類似的經驗,卻不曉得如何處理它。甚至後來是我自己,影片在電影院公開放映的時候,遇到很多年紀比我大的觀眾,可是他們仍在經歷跟自己的家人關係不好、無法溝通的這種困難。我覺得,原來這樣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無論在哪個世代、哪個國家,哪個文化背景的人, 可能都會經歷這樣的情況。所以有很多觀眾都很感謝我分享這個故事,而且他們也很肯定我的媽媽在一個充滿壓力和保守的年代,在這麼保守的地區成長的女性,然後又是同志,她們覺得我的媽媽已經做得很好,她活下來了,用自己的樣子活下來,然後又把我和妹妹兩個小孩養大,我覺得她真的做得非常好,很了不起。我們分享自己的故事,他們不覺得這是應該要收起來的事情,反而覺得是一個把他們療癒的過程, 有些人會覺得想回家做一點事情來改變自己家庭的關係。 我覺得觀眾的這些回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觀眾說的這些說話真的很貼切,都是貼心的說話。可是我跟媽媽說這番話的時候,我覺得她並沒有相信,也沒有聽進去。但是,當這些陌生的觀眾說的時候,我覺得很神奇的是,媽媽有聽進去了。後來在隔年(第二年),因為《日常對話》在台灣的電影院上映了一年時間,然後我的媽媽主動跟我說,希望我拿一些電影票給她帶朋友來看電影。又或是我們有一些媒體採訪和報導,她會收起來,然後會帶出去給朋友看。當時我的團隊都很開心,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是表示《日常對話》得到媽媽的認可,她喜歡這部電影,才會帶朋友去觀看。但對我來說,我覺得更重要的一點是,我看到的是,媽媽已經找到一個方式再次重新理解自己的生命經歷了甚麼。
因為過去的事情,你們在電影裡頭看到。我覺得媽媽要是能夠進入電影圈,她應該是一個很好的編劇。(觀眾哈哈大笑) 你看,她在外頭有非常多套的劇本在描述她的人生是怎麼一回事。媽媽可以跟她的朋友A講一個版本,跟朋友B講另一個版本,可是她從來沒有真的告訴別人,自己的生命其實是怎樣的。她甚至曾經告訴別人我和妹妹也不是她親生的,是領養回來的。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人,你沒有辦法去面對……就是你自己在生命中經歷過的事情,是沒有辦法面對它、也不想去面對它,我覺得是一件很令人難過的事情。所以,媽媽後來跟我說要跟我來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又拿一些報導給她的朋友看的時候,我看到的反應是這一點,我看到她也找到了一種方法,接受了她的新生命是怎樣的。她也不再覺得這是一件羞恥的事情,因此願意跟她的朋友分享。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就是,我會相信當時是跟我們一起看電影的觀眾給予的回饋,為我的媽媽帶來了改變。原因是作為女兒來說,媽媽會覺得你講的是用來安慰她的好聽說話。但如果是陌生人的話,沒有道理騙她吧。所以,我覺得正是這些陌生的觀眾幫了我一把,去完成最後的步驟。所以,我就覺得要非常感謝觀眾。
潘:謝謝。今天來參加分享會的觀眾大約有50多人,而且外面很大雨,也有這麼多觀眾來看你的電影。我把咪高峰給他們發問,看看他們看完之後有甚麼回饋吧。
觀眾1:我在電影裡看到一幕,你剛才也有提及過,你最初是一個人去拍攝Home Video的影像,到了後來就有一個團隊在你家拍攝。尤其是你跟你的媽媽對話的那一場,應該同時是有三部攝錄機同時拍攝,分別是中間拍攝兩個人、一個對著媽媽、另一個對著你。那就變成一個狀況就是,有一些攝影器材在你家出現的時候,你的媽媽的反應有沒有改變?她會否變得抗拒這些攝錄機?
黃:因為好像剛才你提到的那一場告白對話來說,我們那天在現場設置了三部攝錄機,但是沒有攝影師。這是因為我跟攝影師討論過之後,決定用這種方法。原因是我還是會希望現場只有我跟媽媽兩個人。因為我覺得這樣做的話,對媽媽來說,才可以真的比較好一點。對我來說,也許會比較好一點。如果有一個外人在場的話,跟我信任和很親密的人講說話時,我覺得也會有影響。所以,我們決定設置了三部攝錄機,也有一部後備的攝錄機,以妨礙它們出狀況。我的腦袋也會顧慮到這一點;又想到剪接的話,也需要用比較多鏡位,這些都包括在要預先想好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三部攝錄機對我來說也很重要,因為你們剛才看影片,印象可能很深刻。我的媽媽在那一場拍攝的時候,一直說「你怎麼沒有先問人家是否願意就拍攝了」,我覺得很有意思是我之前說過,這是整個紀錄片拍攝的最後一場。媽媽從一開始就知道我們要進行拍攝,又要問她這些事情。可是在最後一場,她看到三部攝錄機的時候,而且她也知道我該問的已經問了、我該說的已經說了,二人之間沒有提到的事情,其實就剩下那件事。所以,她突然開啟了一道防衛的機制,她想那一場對話比較私下進行,可是我越是看到她的反應,我就知道其實我們真真正正就是在這裡,直接實行,沒有化解我們的關係,這樣是永遠不可能改變的。所以我覺得那個其實很大陣仗,用上三部攝錄機,我們唯一一場用上分鏡頭的攝影機,就是那一場對話。對我來說,我也很需要三部攝錄機給我們的壓力,只是我的媽媽要知道這些事情很不容易,可是我要把這件事情說出口的話,可能更加不容易。
其實拍片的人或是觀眾,常常會形容攝影機實際就是一個槍眼。它就像一把槍那般,把它放在人的面前,就會很有威懾性和壓迫感。對我來說,我當時就希望接觸與攝錄機存在的壓迫感,讓我必須把這場對話給完成。所以,我的媽媽在那一場特別感受到攝錄機的存在,其他時候,我覺得是因為已經拍了很長時間,由20歲開始拍攝,直至30多歲,攝影機對她來說,她想不理會的時候,就可以不理它,因為期間我們有試過另一個拍攝方式,就是把攝錄機交給媽媽,放在她的房間裡,我跟她說做甚麼都可以。她想對著攝錄機講話也行,要做甚麼都行。然後她真的是完全無視那部攝錄機的存在,去做一些很私隱的事情,譬如挑腳皮、跟朋友聊天,睡覺時就把它關掉。也就是說,她已經被訓練到可以無視攝錄機的存在。我覺得這樣也挺好,對於拍攝紀錄片的人來說,這是一件很夢幻的事情。當然,被攝者不理會你的攝影機的存在時,是一件多麼美妙的事。我覺得這真的是歸功於她已經很長時間,習慣了有一部攝錄機繞在她身邊。所以她常常叫我不要拍、有甚麼好拍呢,但是我覺得她對攝錄機的存在並沒有那麼抗拒。
另外一個還需要規劃到合作夥伴。我的攝影師其實不是一個做紀錄片攝影出身的人,他真正的背景是做平面攝影。但他也有另一份主要工作,就是在社區組織工作。他算是一個社會運動者,經常跟老人家相處,因為他的社區裡面也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老人家,所以他蠻會跟我的媽媽相處,而且我跟攝影師也住得很近,所以在平常不拍片的時候,他會到我們家來,跟媽媽聊聊天、講幾句話這樣。於是,媽媽已經習慣了、也喜歡這個人,我覺得這其實也會有幫助。她會覺得這個拿著攝影機的人是她習慣的人,並不會感到陌生,因為我曾經有一段很短暫的時間,找了一個來自西班牙的攝影師,他是一個外國人的臉孔,媽媽便會很不適應,她會一直盯著那個攝影師。(觀眾哈哈大笑) 她不是看著攝影機,而是一直盯著那個攝影師,原因是她感到很好奇,因為平常並沒有機會接觸外國人。反而在這個時候, 我意識到這個攝影師可能不是很合適的人選,後來才換了另一個人,因為西班牙攝影師也聽不懂她講的語言,所以我覺得這樣是有影響。我的運氣很好,遇到一個很對的人選,更甚是,我的媽媽也很做自己吧,大概是這樣吧。
潘: 謝謝。關於你的攝影師,我記得有一場戲是你跟媽媽的對談,那一場並沒有用三部攝錄機拍攝那麼厲害,只有一部攝錄機拍攝你的媽媽,然後拍完之後,攝影師並沒有停止拍攝,而且更把鏡頭拉到遠鏡(Wide-shot),看到你在抹眼淚。我覺得這個敏感度是很難得,他知道要怎麼把導演當時的情緒放進片中,作為拍攝紀錄片的人,遇上這樣的攝影師不只是一種運氣、更是感到幸福。
黃:沒錯,因為我覺得……我跟團隊的工作方法也很有趣,因為我不是一個學習電影專業出身的人,所以我跟我的製作團隊溝通的方式,其實是花了很多時間彼此認識和理解。我們也會去討論在電影這個專業上的東西,譬如要選用甚麼鏡頭、我們在甚麼時候進行拍攝、需要拍到甚麼,可是有很多時間,我們其實在聊彼此對於這個世界認識的方法、我們所相信的價值是甚麼、到底為甚麼要做電影。我覺得這個過程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對我來說,他們不僅是我的創作夥伴,包括我的攝影師和剪接師在拍完影片之後,也經常會一起相約去玩,除了是工作夥伴之外,更是朋友。我們就是作為人、互相認識、互相交流;知道對方的故事、理解對方的故事。他們就是真的幫我去完成這件心願吧。所以,我覺得這可能就是自己跟夥伴工作的方法,對於我很有幫助。
觀眾2:謝謝你,你把你家庭的事情能夠用這樣的方式,呈現在我們的面前。我看你的紀錄片在一開始的時候,看見你的媽媽沒有很直接的把她對你們的感受……你問了她很多次,她都沒有說她對你們的感情是怎麼樣。在片末的時候,你叫女兒去問媽媽「你愛我嗎」的時候,她說自己也愛外孫女,影片裡面看到有一點改變。我有點好奇,就是拍了片子以後,她跟你的溝通有沒有改變呢?
黃:謝謝,在每一場映後談,都一定有人會問這個問題。因為畢竟我做這部電影最初的動機,就是我希望這部電影能夠改變我和媽媽之間的關係。我也的確很有運氣,它完成之後,我們的關係也真的有改變,包括溝通的方法有改變。我們從最早……因為我們一直住在一起,然後我在拍攝這部影片的那段時間,把原本的工作辭掉了,每天不用忙碌地上班,有很多時間待在家裡,那我的媽媽也看見了。很有意思的是,她從來沒有問過我為甚麼沒有去上班,又會打電話給我的妹妹。因為妹妹很早已經結婚,她住在離我們家有點遠的地方,我的媽媽就打電話給妹妹,問她為何最近姊姊沒有去上班,待在家裡,她究竟在幹甚麼?即使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是她不來問我,這就是我們過去溝通的方法,就是沒有溝通。然後因為電影拍攝的關係,我們這輩子講話次數最多、最密集的就是在拍攝的那段期間。
拍攝完之後,我覺得很簡單吧,就是過去我們不敢講的那些東西都已經講完了,就好像覺得沒有甚麼不能講,突然發現原來跟對方講話沒有這麼恐怖,那些讓我們害怕的東西已經完結了,所以後來我們的互動會變得比較……我自己的感受是,現在跟媽媽同住在一個屋簷下很自在,不會像以前一樣,你想靠近她,卻不敢靠近她;想跟她說話,卻不敢跟她說話。我覺得這真的如果不是因為這部電影,就不會進行這樣的對話。老實說,如果當年並沒有拍下來,只是我們之間的對話,我不覺得最後會帶來這樣的改變。因為我連自己跟媽媽進行訪談對話的當下,其實我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樣的。我覺得人與人的溝通和對話,是好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雖然我們都使用語言正在溝通,但每個人對於語言的使用,其實還是會有很大的差異和落差。好像我今天講的一句話,你理解的以及我想去傳達的東西,可能不見得是一樣。但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去聽到我們想聽到的東西。我會發現這件事,是因為在我們拍攝提及我的父親的那一場對話,後來我在剪輯台上把這個片段重新看了很多次,才發現我在那個當下,畢竟我是這部電影的導演,但是我終究是一個人,一個平凡、普通的人。我在當下聽到很多媽媽的回應,我在那一刻理解的,也不見得是我媽媽的意思。我覺得如果沒有因為它被錄下來,後來重播再看很多遍的話,我覺得可能這一場對話,搞不好會讓我們的關係變得更僵、更差,而且當下的理解也不是真正的。因此,我覺得自己的運氣很好,因為它被錄下來了,有機會重新再看很多次。我每多看一次,就覺得原來我當時真的是沒有聽懂。
同理對於我的媽媽來說,也是一樣。我們在最初的對話裡,我覺得雙方大概都是在自己的狀態裡,沒有真的在聽對方說甚麼。可是因為它變成一部電影,用一種比較在屋裡現有、其實是很有距離的方式,你看現在或者在當年,我們都有一段距離。你會好像反思多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理解熒幕裡的那兩個人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經驗,因為人原本就是,每個人都是以自己為世界的中心,也是自己所有生命節點的中心,我們很難有機會往後退幾步去看看,其實當時自己到底怎麼了,為甚麼會這樣提問她,為甚麼會這樣回應她。我們不太有這樣的機會去思考,除非你是一個心理學背景或者其他的這種專業的人,你會直接實踐這些方法,一般人不太會的。但我覺得把我的媽媽帶到電影院裡,讓她看我們兩個人之間的對話時,她達成了這件事情。它讓我的媽媽有一個機會,後退幾步來觀看她自己,以及理解我到底在做甚麼、跟她說甚麼。所以,我覺得如果不是因為是用這個形式的話,我都不太肯定我們的對話其實真的會產生後來這一個比較好的改變。
直到現在,我跟媽媽的關係很有意思,我覺得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媽媽在前兩年突然送了一條金項鍊給我,雖然我從來沒有戴它,但在台灣,一般人很少會戴著金項鍊,通常是結婚的時候會戴著它,又或者是台灣的黑道才會戴著金項鍊,(觀眾哈哈大笑) 所以我從來沒有戴過這條金項鍊,我把它送給我的親戚。只是,你收到那條項鍊時,就會明白當中的意思,這是我的媽媽表達她的感情的方式,這是很傳統的上一代人,她們不會用語言去表達心裡的想法,可能感到不自在吧,因為畢竟她們並不是這樣被對待而長大的,所以永遠都是提供物質上的東西,譬如給你買很多好吃的東西、買很多需要用的東西,把一條金項鍊送給你應該就是媽媽的最高等級,都是她的女朋友才有的待遇。我就是因為拍攝這部電影之後,有了金項鍊的待遇。到了現在,媽媽還會跟我的女兒抱怨說「你的媽媽很囉嗦」,因為她有很多老人家的慢性疾病,要吃很多藥,於是我叫她既然要吃藥,那就改變一下生活習慣,她卻覺得我很煩。她覺得以前的我不會干涉她 會比較好,現在就覺得很煩,現在很難有人不理她了,她就覺得太煩了。
觀眾3:I was touched by your documentary. I thought it’s very close and personal. I especially like your close-up camera shots on the faces because it expresses a lot of emotions, it is a solid emotion, also feelings, as I thought the same. (你的作品令我很感動,我覺得它是一部既親密,又關於個人的影片。我很喜歡那些拍攝面部特寫的鏡頭,因為能夠表達出當時的情緒。那些情緒和感受都是很實在,令我深有同感。)
潘:這位觀眾覺得你的攝影做得很好。
黃:我也覺得很好,那個其實也是跟攝影師溝通了。這是因為我早年自己拍攝了十多年,然後當我再次看自己拍攝的素材時,發現了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我剛剛開始拍攝媽媽的時候,會把攝影機用Close-up拍到最近。我自己看到的時候,其實自己第一次發現到也感到很驚訝,因為它完全反映出我想接近媽媽,但在真實生活裡,我並不敢這樣做,可是它被攝影機出賣了。當我一拿起攝影機的時候,我覺得反映了自己心裡面想去做的事情。我心中的渴望就是投放在攝影機上。我就覺得這件事很重要,所以就告訴給我的攝影師。另外,我也跟他說自己經常會看著媽媽。雖然我們一起住,但是你也會挖掘到她的變化。她的臉上的皺紋越來越多、白頭髮越來越多,雖然她會染頭髮,但是「你」看在眼內。我就覺得,那個「你」好好地、仔細地去觀察一個人,「你」是一個人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會希望攝影師也能夠用他的鏡頭,代替人的眼睛去對著我很關心、很心愛的這些人,是有一種像是憐惜的狀態去看這些人。
觀眾4:我想問一下你有否受到日本的一些家庭紀錄片、還有「私影像」電影的影響?還有的是,我看完電影的結尾的名單看到侯孝賢、朱天文、朱天心(註:兩姊妹都是台灣作家,父母是著名作家朱西甯和劉慕沙),他們對於你的紀錄片有甚麼投入和幫助呢?
潘:因為他們看到監製是侯孝賢導演,他對於你拍攝的素材是怎麼樣?他怎樣跟你溝通呢?
黃:其實侯孝賢導演算是一個天使,他會成為我的監製是因為我的故事脈絡,我跟侯導、朱天心及朱天文老師的認識不是因為電影,而是因為我在早前,剛才說過我曾經參與社會運動,我在社會運動的場合認識他們,都是在台灣文壇上的大作家和大導演。因為我當時跟前夫正在參與一個原住民土地的抗爭,侯導、朱天心及朱天文老師來聲援我們。而且,我正在拍攝的那部電影,也是侯導擔任監製。總之,他後來知道我在拍攝關於我家的故事時,那時候是因為日本NHK想合製,但是我沒有電影公司,直到現在也是一個沒有電影公司的獨立影像工作者,後來侯導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他真的非常照顧後輩,我覺得他的心臟很大,我並沒有任何背景,又沒有拍過任何東西,但是他二話不說就帶我到他的公司,介紹他的工作人員給我認識,又說他們會協助我把簽約的事情搞定,所以我才能夠跟日本NHK簽約。然後他說會做監製,因為他知道拍紀錄片找資金不太容易,但是他說「反正我把名字放在這裡,你就去找錢吧,把電影完成」,但我其實不敢,當我募集資金的時候,也不敢說監製是他。我會覺得那個壓力可能比幫助還要來得大吧,當時不太曉得名字可以怎樣使用,真的也不懂。老實說,我也不敢,到現在也不敢,我都覺得還是回到故事吧,因為不可能一輩子都靠誰人的名字幫你做甚麼。後來,侯導幫了我很大的忙,讓我可以跟日本的電視台簽約,更甚是我後來全部資金都是來自NHK,讓我們能夠把這部電影做完。其實侯導給予我百分百的信任,是我很感恩的事情。因為畢竟這不是他的故事,所以他給我一個百分百的信任讓我拿捏;我把這部影片做完了甚麼版本之後,就會讓他過目看一看。他只有在我們要去柏林影展的那一年跟我說,要不我們來看看,然後再剪一個2.0的版本吧。因為我有一個1小時的版本(《我和我的T媽媽》)是給NHK的,然後另一個1.5小時的就是大家剛才看到的這一個版本,它們的敍事結構其實是完全不一樣。侯導說,他也很喜歡1小時的版本,但就覺得想將這兩個版本做一個融合,然後我和剪接師到了侯導的工作室,三個一起再看一遍影片。看完之後,他就搖搖頭說「我覺得這個有點難,不如我還是算了」。所以我們就沒有再進行任何調整,維持現在1小時和1.5小時的版本。我真的覺得他願意為後輩去做這些事情,對於一個新人來說是很感恩而又感動。正因如此,他願意繼續監製我的第二部影片的時候,我也覺得他的心臟也是停頓了,哈哈。
至於朱天文老師她們就是在精神上的支持比較多,因為我們平常都會跟她們聊天。我自己的個性比較不好意思,可能是這樣,即是比較上可以向對方報告下了甚麼努力,然而我很少主動請求對方幫助我甚麼。在創作方面,她們都很鼓勵我們這些年輕一代。
觀眾3:其實您提到那個鏡頭,也是我的一個很喜歡的鏡頭,就是慢慢地打開的。首先看到一個微波爐或者焗爐,然後看到你的媽媽正在工作,往下就看到你,接著看到一堆小孩的書。你在處理自己和媽媽的關係時,往後還有漫漫長路,你跟女兒怎樣相處、自己也有一生要過,好像就是一個短短的鏡頭,就已經有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要感謝攝影師了。因為在那個當下,我已經沒有辦法給他下決定。所以我覺得是他有很足夠的理解來決定接下來要拍攝甚麼,他不見得會敢把鏡頭拉出來(連鏡),他也許就切掉了。所以我覺得就是要感謝攝影師。
潘: 對,攝影師有時候就是眼睛了。
觀眾5: 我想謝謝你的電影,令我也很感動,也會反思自己跟家人的關係。我想問的問題就是這部電影自從出來之後,對你將來的創作會有甚麼影響或改變?
黃:目前還好吧,在創作上覺得還好,因為我不會給自己定型,因為我的下一部片要拍的東西會是另外的題材,但是,不能否認的是這部片的成績挺好,大家也會比較關注我要做甚麼,但是我想有些幫助挺有限,我現在去找下一部片的資金,也是跟大家一樣都很不容易。反而很有意思的是,其實在台灣,很多導演也會接一些商業服務的案子或是甚麼,但別人很少直接找我做這些事。我常常會跟我的朋友說「是不是因為大家看我拍的這部片要拍順序,因此大家不敢找我呢」,因為我發現朋友們都有接很多案子,但就沒有人找我拍這些,因此接案子的工作,我反而沒有這些機會,但我覺得還好吧,反而拍完這部片令我放下了,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就是這樣吧。
觀眾6:黃導演你好,我看了你的影片之後就特別喜歡,我覺得全片都是非常溫婉、流暢,很自然。最打動我的一幕其實是在最後,就是你女兒的說話。你的女兒最後問出了你憋在心裡的那個問題,就是「媽媽到底愛不愛我」,其實我看到最後也是有一點偷偷的抹眼淚。我覺得以全片來說,其實紀錄片是沒有一個明確的故事線,但就有一條暗線能夠一直把觀眾從一開始遷延到後面,延長吸引我們的注意力。我想問一下你關於創作的這方面,當時在設想的時候有沒有提前準備一些拍攝內容,或者是你怎麼去準備的?因為也知道如果真的是等待生活中的每一個瞬間,能夠成為一部這麼精彩的電影作品,能夠被採用其實是一個概率很低、也很難創作的事。所以我想請教一下你關於當初的自己的設計、一些創作方面的心得,有沒有東西能夠跟我們分享一下?
黃:我的工作方法可能挺混合,我也會做一些非常基本的工作,譬如會去想怎樣去建立人物,這是一個基本步驟吧,要怎樣建立人物,使觀眾認識人物的特點、他的特別性格,這些東西我會記住,就是做這種很基本的工作,我也會去做。可是我覺得在這些基本的工作之外,我覺得自己一直沒有忘記的就是,到底我真正想講這個故事的最根本的東西是甚麼。只是,我雖然也會做這些基本工作,譬如我還是會寫一些故事線,包括「三分鐘概念」的那些是有的,又想過應該怎樣做。可是覺得你雖然懂得這些規則,但是不見得一定都要依照這些規則去走。對我來說,我常常覺得自己不是一個會把觀眾放在第一席位置的創作者,但是《日常對話》有點特殊的是因為這部電影對我來說,最重要的觀眾只有一個人,就是我的媽媽,所以我會一直想到母親。另外一個就是到底我要怎樣講,令我的媽媽也能看得懂,可能是比其他事情還要來得重要。所以,我常常要把這兩邊都要顧及,不是去接合它們,但它們都是一起吧。我也會去思考影像的語言是怎樣,可是我不想要的方式,只是去遵守這些所謂的電影規則。因為我當時在製作期間,就有聽過很多前輩分享,有些人很有精準度,他們在分鏡表裡會標記,在第幾分鐘,他們的觀眾會拿出第一張紙巾抹眼淚這樣。當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覺得非常不可思議,那的確是一個能夠訓練出來的能力吧。但是對我來說,我做電影為的不是這樣,我沒有好好地、老老實實地面對我自己,然後再把它給轉譯出來,給我很重要的人能夠接收到,這個對我來說可能是更重要。所以,當後來那些很基本的工作、那些便利貼,後來其實都放到旁邊去了。因為當後來我們的工作方法是,我先給我的剪接師一個版本,但是那個版本不是一個「死」的東西,我可能只是寫了前面幾分鐘,為了幫助我的剪接師能夠比較快進入我這個人的狀態,我覺得這樣應該有幫助吧。我的感受是感到舒服和自在,這樣才是最重要的。其實我覺得做紀錄片很幸福的一點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種可能性,不管是在媒材上面,或者講述的方法,我都覺得它應該是一種最自由的電影,更何況我也不是一個電影科班出身的人,所以也有很多規則是我肯定不懂,所以我就覺得這樣真的非常好,只要忠於我自己就行了
觀眾3:這不是問題,是一個觀察。我的英文比中文好,所以剛才我用英文問問題。我當初聽不懂台語,所以需要看字幕。我第一次看的時候是看英文字幕的,然後把它跟中文字幕比較的時候,就覺得很不一樣,所以我覺得中文字幕做得比較好,英文字幕的翻譯有點不怎麼好。
黃:好的,我們有討論過這件事情,因為幫忙翻譯字幕的人從小在美國長大,我們當時也有做過一些抉擇,到底是要翻譯得非常精準,但是字幕可能會非常長。只是對我來說,我選擇了用相對簡單的英文,原因是影片之後可能會給很多觀眾看,他們都是以英文字幕作為基準。我自己也不是英文非常好的人,對我來說,只要語言內容沒有錯誤, 能夠理解到就可以,因為我覺得更重要的其實是影像與聲音的傳達。如果把字幕翻譯得非常貼近和精準的話,我會覺得大家好像會只看字幕了吧,哈哈。這樣確實是當時的抉擇,但是之後有機會也可以調整。
潘:OK,我們用熱烈掌聲給黃導演,我們期待你的第二部長片,要不要等幾年才有,還是很快就能夠看呢?
黃:你知道我正在拍攝第二部影片,希望不要那麼久,但已經很久了,因為我是從2008年開始拍攝到現在,已經是很久遠的事了,希望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就是明年或者後年我能夠把它完成,不然我一輩子能拍的片子都不太收(票房)了。
潘:那就幾部一起拍吧。
黃:那就很希望很快可以帶第二部影片給大家看。
潘: 我們很期待你的第二部長片。謝謝你,謝謝觀眾,拜拜。
黃:也要給一些掌聲給潘導演,謝謝大家。
簡介:
黃惠偵導演由六歲開始跟著媽媽跳陣頭,二十歲轉行從事社會工作,開始學習紀錄片。曾任台北市紀錄片工會秘書長,現為自由影像工作者及一個孩子的母親。過去作品包括《我和我的T媽媽》、《八東病房》及《烏將要回家》等短片。
與談人潘達培是資深紀錄片編導,現為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專業應用副教授。曾為香港電台電視部旗艦節目《鏗鏘集》拍攝紀錄片二十多年,作品逾百齣,屢獲國際電影及電視節獎項。除紀錄片外,潘亦監製青年人節目,透過跨媒體計劃,鼓勵青年人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