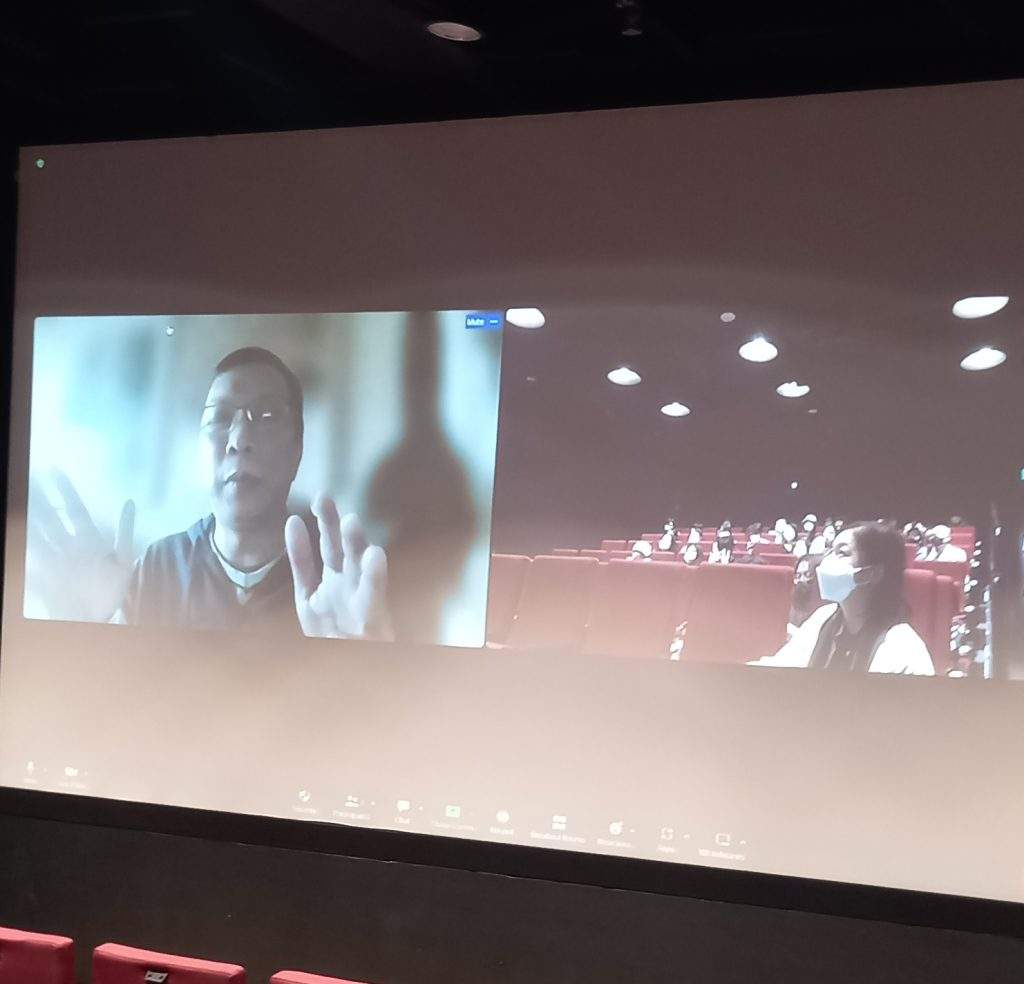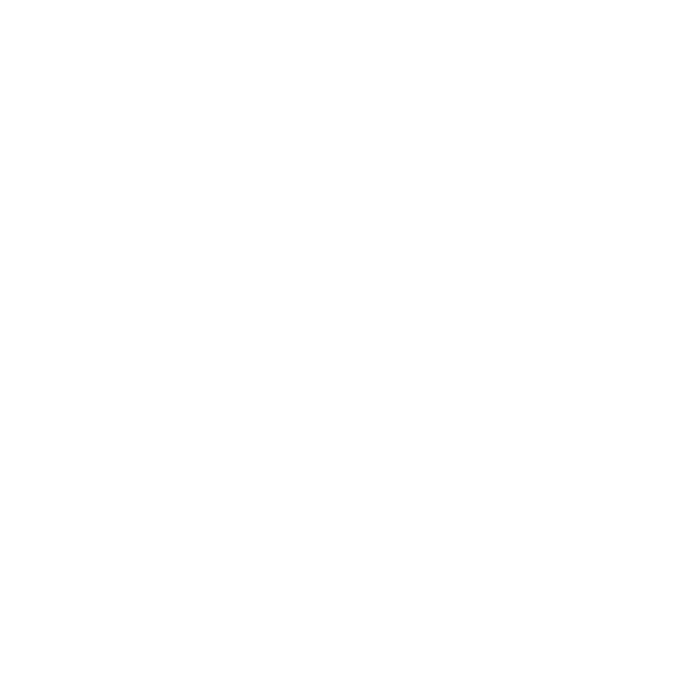【喜舊創新:紀錄片的創作與賞析】 2月19日《本來面目》映後座談節錄
2月放映活動以「人物傳記」為主題,放映紀錄片《尋找小津》、《這不是一部電影》、《本來面目》及《赤手登峰》。 四部選片以不同方式呈現公眾人物的故事。
我們邀請執導《本來面目》的張釗維導演在2月19日出席映後座談,分享他拍攝一部關於台灣法鼓山創始人聖嚴法師的紀錄片的歷程與感受。《本來面目》是法鼓文教基金會和CNEX共同製作,張釗維導演由2017年開始拍攝計劃,製作歷時三年,用影片和動畫講述聖嚴法師的生命故事。
主持:請你跟觀眾介紹一下這部紀錄片的起源?
張:主持人提及到我的上一部影片作品是《沖天》,是在2015年完成的,是關於抗戰空軍的紀錄片。到了2016年的時候,我在一個心理分析的研討會上,當時《沖天》是討論對象,就在這個研討會上放映。在那裡,聖嚴教育基金會的執行長楊蓓教授,她在台灣是一個很資深的心理諮詢專家,同時也是聖嚴法師的弟子,更是基金會的執行長。然後,這部影片觸動了她有一個想法。聖嚴法師在圓寂之前曾經跟楊蓓說,請她幫助寫一本關於他人生的一個專輯。楊蓓老師之前還沒有完成聖嚴法師交代的功課,一直到她看了《沖天》時,就覺得也可以用紀錄片的方式來完成它。一直到2017年時,她跟我談到想為聖嚴法師拍攝紀錄片的想法,同時也因為2019年是他圓寂的十週年,希望能在到時候可以完成(紀錄片)。所以,我們就是從2017年開始進行一些前期調查及拍攝,最後在2020年完成,疫情期間在台北進行首映。
這部紀錄片是關於聖嚴法師的一生,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時間點。剛才聽你提到這部影片從調查、拍攝到製作,大概是用了三年時間,但裡面是包括大量歷史資料及素材。你當時是怎樣處理這麼多資料呢?
張:是,其實聖嚴法師留下了非常多資料,包括他自己早年撰寫的很多著作,甚至有他前半生的自傳,這些都有。有人整理了他的年譜,是非常厚的一本年譜,還有的是包括相關東西,包括日記,我們很難得有一個機會可以看到,因為他的日記是不對外公開的,其實是有非常多材料。
我初步閱讀了他的著作以及年譜之後,突然意識到有一個現象,聖嚴法師80年的人生裡面,每逢「9」的那一年,就是從1939年直至2009年,2009年是他圓寂的那一年。對他的生命來說,每逢「9」的那一年,都是一個很重大的轉折點。所以,我很早的時候就想到以每十年為一個節點,來建構聖嚴法師一生的故事。至於一些相關歷史材料和片段,基本上也是用每十年為一個節點來搜集的。
主持:聖嚴教育基金會是本片的出品方,你們對於怎樣呈現聖嚴法師一生的故事,即是在他的個人故事的層面,你們當時是怎樣溝通呢,還是大家都同意用你的每十年為一個節點的方法來呈現呢?
張:是的,剛才提到的楊蓓教授是推動這個計劃的最核心的人,她是監製。她從一開始就跟我說,對於這部影片的期待只有兩點,事實這些不在話下,但是,有兩個重要的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希望能夠讓不論是聖嚴法師、甚至是非佛教徒都會願意來看這部影片,不是只拍給法鼓山的信眾看的。第二個原則,就是不要把聖嚴法師描繪成一個高高在上的、一個好像超凡入勝、要去膜拜的對象,而是用一種平常的眼光去看這樣的一個人的一生,把它回到一個人的身分上面看。但是,這一個平凡人、出家人很努力地去做了一些事情,就是這兩個原則。除此之外,她都非常尊重我們,不論是一些敍事框架、使用影像的風格,這些他們都非常充分地尊重。到了後期的時候,這部影片的築建、形成的時候,也有一些比較內部的反饋過來,這些的話,我們會在原來的框架底下盡量吸收。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主持:本片也有一部分片段是以動畫方式來呈現法師生命裡的一些片段,譬如他小時候的經歷、他出家的經歷,就是有很多不同片段都以動畫來表達。你可否跟觀眾介紹一下,為何會選擇那些片段呢?動畫製作的過程是怎樣的?因為那些是由專業動畫師製作的。你作為導演,會怎樣跟動畫師溝通呢?
張:其實動畫的做法,我在《沖天》的時候已經用過,當時是用真人演出、人工手繪的方式去製作動畫。各位觀眾也可以看一看《本來面目》的幕後花絮片段,當中也紀錄了動畫拍攝及製作的過程。選擇動畫方式是因為我們缺乏一些畫面,當中有很多重要的故事點。譬如他小時候在江蘇,還是跟父母一起的時候、還沒有出家的狀態、剛出家時的狀態,然後是到了台灣之後的狀態,法師其實有很多文字描述。我在想,應該怎樣把這些文字描述變成視像,能夠讓觀眾用影像方式去理解、感受到法師的狀態呢?所以,我把他前半生的事件,採用動畫表現出來。基本上是在他50歲之前的過程裡面,選了幾個節點來做動畫。
《本來面目》幕後花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nTMosJ9eYQ
由於他50歲之後,已經留下比較多照片或者錄影片段,所以基本上不太用動畫。大概就是這樣的做法。在真人演出的時候,演員都是真的在法鼓山修行的法師和出家人,由他們飾演聖嚴法師和他的師父。所以在這個過程裡,我們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因為是跟一班出家人團體合作。不過這些法師都做得很好,很精湛,各有個性,他們也充分地表現出各個人物的性格。
主持:這部影片在最初的時候,我記得(你)有一個想法就是訪問他的弟子果忍。在那段訪問裡,你問他一個問題,就是他認為聖嚴法師有沒有尊嚴。對你來說,你把這段影片放在前面,是否想去呈現「尊嚴」跟聖嚴法師是有一種很密切的關係?因為在之後的片段看到他建立法鼓山之前,經歷過很多很重要的歷史事件、戰爭等等,也有看到他對於當年台灣佛教缺乏人才,對此感到灰心,於是後來到日本學習。關於「尊嚴」這件事,把它放到影片的開初,是否想呈現出這樣的面向?
張:的確是。因為法師的一生經歷非常豐富。從大陸出生到出家、然後在1949年因為戰亂,跟著部隊去到台灣,然後還俗、之後再次出家。他的經歷也相當豐富,到日本留學之後又到美國去。他在90年代的時候,足跡遍佈全球各地。我在想,當我要去描寫這樣的一個法師的時候,一方面我又不得不去關注到他身為一個佛教的傳法人或者是出家人的身份,以及由他隨之而帶來對於佛教概念的吸收、消化與傳播。但是,我不能夠放棄這個東西,畢竟這是一部關於佛教和出家人的影片,然而不能一下子就掉進了一些「名項」,即是專有名詞裡面,例如「農禪」、「放下」,可能一般人會聽到的這些佛教語言。可是,我就開始在想,自己該怎樣找到一些相對世俗化和通俗的概念,能夠跟聖嚴法師的一生,以至佛教理念當中要傳達的一些概念,可以互相結合的東西?後來我就找到「尊嚴」這個概念……原因是在我在看法師的專輯的過程裡面,他說自己當初出家的時候,有一個很深的體驗。他大約18、19歲的時候,意識到佛教這麼好,知道的人卻那麼少,誤解它的人卻是那麼多。他建構了一種意識,就是在民國一直到戰後時期,中國佛教有一個跌落谷底的狀態。而這個跌落谷底的過程其實經歷了300、400年,從明末以來一直往下跌的過程,跌到他出家的時候,當時整個中國的佛教遭遇到最大衝擊,然後沒有地位、失去尊嚴的一個時候。因此,我希望透過聖嚴法師的生命故事,在這部影片裡傳達「尊嚴」的概念。
所以,主持人剛才提到影片一開始的片段是訪問那位美國弟子果忍,是當時在他身邊的弟子。其實我有問他,1979年的那個春天,當時大約是3月,大雪紛飛,果忍跟聖嚴法師一起在紐約街頭走來走去,其實他們當時並不是沒有地方住,只是住的地方每天不一樣,可能沒有固定住處,身上的錢很少,有些情景甚至比我在影片裡呈現的可能會更加凄涼,舉個例子說,他們可能到垃圾桶裡面去翻剩菜出來吃,有那麼幾次會是這樣。所以,他的情況從我們外人來看,就像是流浪漢的感覺。所以你看在影片一開始的時候,設計了在美國街頭有一個流浪漢的景象,其實是一個對比,或者是一個連結。至少我看這一段故事的時候就會想說,外人看起來聖嚴法師是住持,非常有尊嚴,又或者說是其實我們一般人在路上看到一個出家人在托缽的時候,不知道多少人會覺得他做這個行為時很有尊嚴。因此,其實我訪問果忍,請他回應這一段(經歷)的時候,特意問他這一個問題,就是他覺得師父當時是否還可以保持他的自尊?他就回答了,我就把這段訪問給剪進去。的確,「尊嚴」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於聖嚴法師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心理內在的自稱,包括他後來出國留學,其實,他很有那種知識分子的自尊,但是知識分子的自尊……太多的自尊就會變成「我執」,所以他在日本的師父也有在棒喝他。師父曾經向說法師說,他身為一個出家人,為甚麼要去唸博士學位呢? 這樣其實是棒喝他要放下所謂知識分子的自尊。但是要怎樣從這個東西,又不是完全粉碎它,也不是從這個東西能夠象徵到另外一個層次的尊嚴,對於「求道」這件事情的尊嚴的一種追求,這就變成他一生當中,一個階段接一個階段的功課。
主持:製作這部影片的過程,對於你的人生或者信仰有否帶來啟發或改變?因為影片裡可以看到聖嚴法師縱使遇到很多困難的過程,他也很清楚自己在幹甚麼,然後一步一步創立法鼓山,就是一個信仰的歷程。
張:我覺得自己每拍攝一部影片的時候……經常說拍紀錄片就是這樣,無論是現實題材還是歷史題材,都要花很多時間。《沖天》花了兩年,《本來面目》花了三年,意味就是必須跟那些人物在一起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你一定會從他們身上學到一些東西,或是獲得一些體會吧。所以,每一次拍攝影片對我來說,我覺得是他們帶給我一些人生上的增長。《本來面目》這部影片其實對我的人生有一個蠻關鍵的作用。 其實我拍攝這部影片的用意並不在於要去弘揚佛法或是法鼓山,而是希望盡量回到去說一個出家人從小到大的故事,大概是這樣情況。因此不要有這麼強的佛教色彩。但因為他是出家人,所以也有佛教色彩。
我在拍攝的過程裡,自己在拍攝之前也有接觸過一些佛經,我的家庭也有佛教的傳統。老實說,我也是法鼓山的皈依弟子,是在2004年皈依,但不是那種很認真的弟子。我會到法鼓山,但就沒有很認真去學習。所以,我當時的感受就是覺得佛陀是我的老師,但我並沒有那麼清楚地去知道自己是一個佛教徒,或者要去皈依一個宗教的感覺。拍攝完《本來面目》後,我的最大變化就是會覺得自己是一個佛教徒。雖說我依然是一個不認真的佛教徒,但我相信它作為一個宗教,它有很多價值。我們先不說它解決現實世界、社會上的這些問題,甚至讓我怎樣面對自己,我解決自己內在的一些問題,它提供了一些方法。
由2020年起,當時疫情開始很嚴重,一直到現在,這個東西對我的感覺就是越來越深。你如何在缺乏當中找到自己的安定呢?在這個過程裡,我如何從缺乏裡面學習到的一些體會或認識,能夠將之應用在工作或者生活上面呢?這些都是在我製作《本來面目》後,並不是一下子就變了,或是突然間翻天覆地,而是一個點點滴滴變化的過程。
所以,我有時跟朋友談及本片時,其實我並沒有想要傳教,沒有告訴觀眾說佛教有多麼好,但我跟朋友們聊天時會說,若你有機會,譬如你遇到一些問題,試著去打坐吧, 或者去做禪修。而在西方國家,人們就會去練習靜觀(Mindfulness)之類的東西。不一定要跟佛教完全有關,因為有很多不同的療癒方式。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他們都會做一些類似的事情。 但是,這些東西對我來說,就是我自己的心願,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是帶給我一些點點滴滴的變化。所以,這個就是我覺得《本來面目》這部影片對於我自己而言,也可能是我一輩子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影片。
主持:為甚麼這部影片會用蘆葦草隨風飄動的畫面作為首尾呼應呢?為何你會採用這個情景呢?它跟法師的生命有甚麼含意呢?
有蠻多觀眾問過我這個問題。老實說,我並不是很仔細去思考蘆葦草在哲學上的意涵、文學上或者言語上,蘆葦草是有它的意義。其實當時我會使用蘆葦草,起初我們開場的設定就是比現在各位看到的更加複雜一些。 但它有一個共通的東西就是我們想讓觀眾去感受到聖嚴法師出生和成長的地方就是江蘇南通 ,它在長江北岸,跟鎮江相對著。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呢,那裏就是有一大片的蘆葦草在江邊生長。所以,其實我一方面是想去呈現這個東西,就是去呈現聖嚴法師在怎樣的地理環境裏出生、長大。另一個就是,在我的原本構想裏,我想透過蘆葦草的一些光影效果與形象, 映照出一種夢境的感覺。各位如果讀過佛經的話,就會知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電亦如露,應用如是觀」這句話。很多學佛的人都會說人生如夢;蘇東坡是一位居士,經常提及人生像夢,也經常提到夢。我當時也試圖用蘆葦草的這個畫面來映照一種夢境的感覺。當然,這個夢境的感覺後來就變成比較只是點狀,並沒有很系統地把它延伸出來,因此是比較點狀的一個過程。我現在只能告訴你們就是蘆葦草這個事物的來源,大概是這兩個了。在影片裏面,就是比較點狀的呈現。
觀眾1:導演你好。我想請問聖嚴法師有一個構想就是建立法鼓山,把他師父東初禪師的思想延伸,而且當時是不是被迫搬到別處建立新的道場?為甚麼會這樣?
張:這件事其實並不複雜, 當時因為原本的那一間農禪寺,首先在80年代,聖嚴法師主要以農禪寺為他的基地。其實,農禪寺當時在台灣算是一間違例建築(僭建),理論上因為那一片土地應該是農田,當時作為農禪寺的幾間屋就是農舍,那裡不應該是用來做寺廟的用途。大約在1989年,台北市政府要重新規劃土地,也要重新規劃那裡。於是,農禪寺當時就變成一個問題,它很可能會被拆卸。因此,聖嚴法師就要趕緊去找一個新地方,即是後來的法鼓山。事實上,他後來建成了法鼓山之後,原本的農禪寺並沒有被拆掉。那麼,用甚麼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呢?就是經過一些協調後,台北市政府把它變成一個古蹟。由於它變為古蹟,因此就在法例上,可以改建成為新寺院。因此,到了後來2009年的時候,農禪寺的整座建築重建,如果各位有機會去台北的時候,農禪寺變成一個很漂亮的地方,有一個大殿名叫「水月道場」,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
觀眾2:導演你好,首先感謝你拍攝這部作品。因為我本身就對聖嚴法師 或者法鼓山不太認識,只是知道法師很有名。今天看了這部作品之後了解到很多。其中有一個很觸動我的地方,就是「放下」這個概念。然後我想了解一下,因為這是紀錄片,肯定拍了很多東西,有沒有一些片段或者已經拍攝的東西,由於概念上或電影片長問題,所以沒有放進去,但其實也很值得跟觀眾分享的呢? 我還想了解一下這部影片在2020年完成,在這麼多地方、這麼多次放映之後,觀眾的反饋對於你一些新的印象是甚麼?
張:我說一個沒有放進電影的東西,的確由於時間和長度關係,所以我們必須捨棄。其中一個是關於果谷,他一開始是法師,後來還俗了,各位記得嗎,他坐在蒲團上面接受訪問,又說過要不要下地獄的那位菩薩。其實他現在身處柏林,他很喜歡打坐。果谷菩薩年紀很小就已經跟隨聖嚴法師在美國(修行) ,因此他很喜歡打坐。可是到了後來他出家之後,發現師傅會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鍛鍊一班弟子。他喜歡打坐,但師父卻叫他不要打坐,反而派他到廚房去煮飯。如果總是喜歡跟別人說話,就會派他帶到一個安靜的地方,沒有很多機會跟別人說話。若是那種很喜歡活動的人,師父會把你派到一個不用很多活動的地方去。我訪問果谷菩薩的過程裏 ,他提及很多這樣的例子。就是一種禪宗的鍛鍊,完全跟你的原有個性是相反、調過來的,就像動畫裏面,有一段就是聖嚴法師的師父東初老人要他在大房間、小房間之間不斷轉換的故事。師父不斷用這樣的方式,去鍛鍊弟子的心智。 這個東西直到今天,我想在法鼓山還是存在的,就是這種鍛煉的方法。即便是其他禪宗寺院,不一定是禪宗,可能是其他佛教寺院也有存在。這個東西對我來說,影響是很深刻的。
在不同的地方,會有不同的反饋,但是,有一大部分都很類似,就是對於聖嚴法師的生命有一些更多的認識。然後有一些反饋會是……本片在中國大陸放映超過30場,包括線上及線下的放映,也在好幾個城市都有放映過。 我覺得很多時候的反饋是會連結到自身的經驗。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年輕人、中年人,或是年紀比較大的人,在這部影片裡,或者在聖嚴法師的故事裡,你也好像會找到一些跟現在自己會面對的一些問題也好,或者是人生的一些階段也好,都有一些相應的地方。
我舉一個比較有趣的例子。在台灣放映的時候,有個製作經驗豐富、又有拍攝過紀錄片的導演來觀映,他大概四十歲左右,也不是佛教徒,而且對聖嚴法師興趣不大。他跟朋友一起來觀賞電影,我跟他挺熟,不過沒有推介他看影片。他本來也沒有甚麼期待。當他看完之後,當中有一個東西觸動了他。
各位記得嗎?在影片的中段,聖嚴法師說了一句話就是「生命的目標,需要有一個大方向,作為自己永恆的歸屬。能夠建立這樣的目標,人生不管是短或長,都是非常的有尊嚴。」 來奠定我們作出選擇。 這麼簡單的一句話,令他有很深的觸動 。他跟我說,因為他是公司老闆,恰巧當時要跟員工進行年度考核,每個人都要跟老闆一對一面談。他會問員工今年的工作怎麼樣、下一年有什麼期望、希望能夠獲得怎樣的待遇,或者想達到怎樣的目標之類。那個導演跟我分享,他在2020年的面談裡,向所有員工問了同樣的問題,就是問他們的人生大方向會是怎樣。我就覺得很有意思,這其實並不是大道理,但這部影片在某程度上,有些地方會跟你當下的某種內在需求是相應的。而且,你在不同階段再重新看本片的時候,那個相應的地方會是不一樣。我就是在2020年開始放映之後觀眾給我的反饋當中,有很多這一種感受。但是,我覺得有些相應(的地方)是他們也不會很明白地說出來,因為有些東西很私密,他們內在的感受被啟動了。
有時候,我也會看到一些觀眾在哭、淚流滿臉,我也不好意思去問他們為何會哭泣,哪裡被觸動了,因為那是很個人、私密的一些內在感受。甚至那個觀眾也不一定能夠說得出到底為何會這樣。所以,其實在中國大陸(放映),我也遇到一些觀眾有這樣的反應,大概是這樣的狀態吧。
簡介:
張釗維導演是台南市人。他曾任職《破週報》編輯、《南方電子報》主編、公共電視特約編導、新加坡運行視覺製片人、香港陽光衛視紀錄片總監。2006年參與創辦CNEX,擔任製作總監迄今。目前亦兼任北京視襲影視首席內容顧問。文字作品包括:《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1970年代台灣現代民歌運動史》、《穿梭米蘭昆》、《真實的支點》。《本來面目》是他耗時三年製作,於2020年公映的紀錄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