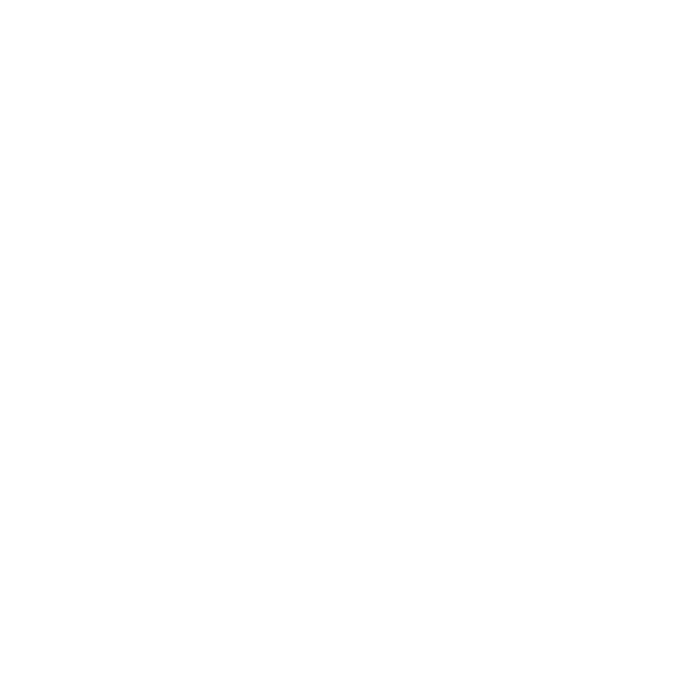【喜舊創新:紀錄片的創作與賞析】12月10日《絳紅森林》映後座談節錄
【喜舊創新:紀錄片的創作與賞析】於12月以「群像」為主題,放映紀錄片《絳紅森林》、《差館II》、《艾格妮拾風景》(The Gleaners and I)、及《犴達罕》。 四部選片以觀察方式,呈現一些因為各個原因而連結在一起的眾生相。
12月10日,我們邀請金華青導演與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研究助理教授陳智廷博士線上進行映後對談。《絳紅森林》是內地導演金華青於2021年完成的紀錄片作品,紀錄了在遼遠的青藏高原,有近兩萬名的女性修行者「覺姆」棲身於亞青寺。在每年最寒冷的日子裡,一幫覺姆在狹小的木屋裡閉關修行,長達六個月的聽經考試,幾乎貫穿了她們漫長的冬季。當「和諧發展」的口號進入高原,遺世獨立不再,覺姆與上師含淚道別,即便肉體將逝去,心靈仍要像一座大風吹不動的山。在靜謐純粹之地,《絳紅森林》展現了身處其間,在精神世界裡上下索求的踟躕靈魂。
金華青:金;陳智廷:陳;現場觀眾:觀眾
陳: 關於這部電影,我在閱讀這部電影的影評時,有一個影評提及到它不僅是一個民族誌,同時也是隱祕的哀歌。在這部電影當中,其實是給觀衆的視覺震撼,不管是攝影、光影,然後構圖,就是可以看到在一個被雪上面的城市。然後我想請導演聊一聊片名,爲什麼決定說這部電影名叫《絳紅森林》? 我們可以看到是因爲覺得覺姆他們穿著的那個絳紅袈裟,在這部電影是一個主要的視覺元素,請你說一說片名。
金:《絳紅森林》,首先從這個片名的本身來說,因為森林一般來說都不是絳紅的,如果是用《絳紅森林》的話,給別人首先有一種猜想的感覺,為甚麼森林是絳紅呢? 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森林,每一個覺姆都是一棵樹,好像是每個人都在這個廣袤的荒原上。然後這個「森林」在我的眼裏就是一片宗教都市,後來就被全部砍伐,就是這樣。
陳: 這部電影其實是從2014年開始拍攝,然後歷經了6至7年的拍攝時間,我知道導演也曾經到不同的地方去提案,也參加了一些創投會議。你可否跟觀眾分享一下這部電影的創作歷程? 為甚麼導演會對這題材有興趣? 如何去規劃整個拍攝的一個想法?
金: 其實一個導演他自己或許不是特別清楚喜歡的是甚麼,但是內心是知道的,但更多的時候是無法用文字來把它描述出來,或者說他不會經常跟別人講,或者是審查說自己應該喜歡甚麼樣。但是,當你遇到這樣的選題,你到那一刻便會很清楚「我要拍這個」。我記得這個選題,我好像決定拍攝只用了幾個小時。然後我用了一兩天,自己在思考當中走,然後告訴自己怎麼去「構想」,好像只用了一兩天吧。
但是為甚麼用「森林」,就是中間停了好長一段時期,就是跨度幾年,拍攝了應該是五年多,中間停了兩三年吧。我們當時以為它肯定也拍不了…可但是不知為何,我們就進來了(亞青寺),得到了一個機會這樣拍下去,因為主要是不允許吧,是當地的政府,包括寺廟都不允許。
我們都很尊重她們,就是覺得一個地方好像被外人打擾,是一件很不尊重的事情,或者說在這個地方拍攝是不可思議的。但我們又很想拍攝,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怎麼辦呢?我們的拍攝影響她們的修行。而我們作為一個創作者來說,又像是為了一個作品,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就是這樣。所以就是在磨合、等待,那怕被允許之後,他們能夠接受我們的影像也需要很長的時間吧。
陳: 其實這部電影也真的是蠻厲害,因為剛才導演提及過在拍攝上也遇到了很多阻礙,因為在這部電影當中,不管是性別、民族,宗教之間的交集,包括在亞青寺,其實它的地理位置一般人是很難進入,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你是怎樣到達那個地方?在拍攝過程是怎樣跟他們溝通,取得她們的信任,然後進去拍攝的呢?
金: 以前去的話應該蠻方便的,雖然那裡路途也比較遠,是從成都過去的,現在交通方便很多,原本也要翻山,從成都出發到康定州,一直往裡邊走很遠,確實很遠。現在可能是因為一些政策的限制,不一定能夠進得去,我也不太清楚,已經兩三年沒有去了。
還有的是我們怎麼讓對方能夠接受我們的拍攝。除了她們(覺姆)的允許之外,其實每個地方也需要別人的允許,例如天葬,那就要天葬師允許。我們進入經堂,就要經堂的管家允許。我們到覺姆的小房間裡面,就要她們的允許。每到一個地方,就要經過一個具體的人的允許,這樣的工作量會非常大。比如說我們拍閉關,我們在2014年10月去的時候只是看一看,離得很遠很遠。然後再過幾年之後,一年比一年好一點吧。她們從內心當中也能接受你,例如她們一開始會覺得你只是個遊客、只是來拍攝,她們便會不高興。後來發現你又來了,然後再過一兩年,你又來了,再過三年、四年,你又出現了。她們也很多次看到我們在冰天雪地當中,就是當她們要在那裡打坐很久,我們也坐在邊上聽,我猜想她們便會覺得這個人到底是為甚麼? 她們在廚房裡的時候,我們也很早在天未亮的時候也過去,她們在斜道邊上等,我們也在邊上等。慢慢地,她們會覺得至少你是沒有敵意的,或者說沒有過度影響她們,因為我們一直都沒有動。然後我們就會問她們很多規章,就一點一點的、慢慢的,然後好拍的先拍,難拍的就後拍,一點一滴的。
陳:關於這部電影的聲畫關係,有個處理是很特別的,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覺姆伏在地上聆聽上師的指導,上師是以畫外以聲音的方式呈現,請問當中拍攝的時候,是有甚麼樣的禁忌? 還是你在美學上的選擇?
金:當時那個地方一共有12個「堪布」,也就是有12間房子,名稱叫作「昭覺寺」,就是得到昭覺。我們認為也叫「覺昭」,是密宗,就是得到「覺」、「昭」之意。但真正允許我們拍攝的只有2位,一位是男上師,另一位是女上師。女上師是打卦為主,而男上師是教學為主,好像是這樣。「堪布」意思是老師,我們會稱他為大學的教授。為甚麼我沒有拍攝那位男上師的原因是,第一,你們看起來會覺得全片好像沒有住持,沒有所謂方丈、住持,好像是校長似的也沒有。教學人員也很少,因為都是男性,在我的眼裡,我好像不想把鏡頭對準他們。
其實這位「堪布」,即是男老師,他很願意被我拍攝的,但是我一直都沒有拍他,為甚麼? 我也不是特別明白,好像就不太願意把鏡頭對準去,就是這樣的意思。我能希望拍到反應,然後每次都是拍攝他的反應,後來就慢慢覺得好像就算了吧,不拍他了,就是畫外音吧。但是那位女老師是出現的,可能是因為她戴了一副眼鏡,真的,我的內心想法是這樣的,她戴了一副金絲眼鏡。我就不太喜歡這個寺廟裡出現的一些元素,比如是水泥地,一些現代的東西,當然這些想法只是我的個人愛好而已,包括覺姆在考試時用的那個話筒(咪高峰),我的內心好像有點抗拒,但我又說不出來為何要抗拒它。那位男老師也戴上一副眼鏡,可是我不想拍他。可能是因為我覺得這座寺廟是想像出來的一個地方,我希望它是怎樣的。所以,我們在每個鏡頭都希望他避開,這就是攝影師的…不知道吧,就是拍出心裡面的感覺。
陳:關於心裡的感覺,其實在全片當中,我們也看到使用了很多Wide Shot,所以看到是比較多全景,看到整個環境,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呈現群像。以下這個問題是,請問導演你在創作上的選擇,就是為何想要選擇呈現群像的方式,而非聚焦個體的方式進行創作?
金:有兩個方面吧。第一個方面是從操作的程度去想,就是很難找到一些個體。為甚麼? 第一個是因為她們管理很嚴,若有一個覺姆能夠允許我們拍攝的話,她自己還是需要她上面的老師同意。第二個方面是,我覺得是如果是一個修行認真的人,她不會給我拍攝的,她不喜歡我跟在她的身邊。所以我不想拍攝一個非常懶惰的人。就是說,真正修行的人是很認真的。
另外,她們沒有手機,我找不到她們。其實那個時候去藏區,第一次去的時候,我甚至認為她們是男生,好像是男性、很多人,但是他們告訴我確實這些都是女生,所以說,其實我根本沒法辨清楚誰是誰,或者說在哪個時間段能夠找到那個人。比如說我今天看到她,她一走,我就找不見她了。
當然這個難度是有,但並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甚麼?我為何沒有拍攝個體的原因是,我還是想跟她們保持距離。為甚麼呢,就是我們所喜歡的是被震撼到的群體,像整個群體我會震撼到。
我其實並不了解她們, 比如說有人會問我在影片當中,為甚麼沒有交代她們為何會以藏傳佛教為信仰?為甚麼會來到這裡? 那麼她們現在想甚麼?其實我覺得,我個人的感覺是我跟她們是不一樣的。那怕我們知道答案,也並不代表我們真正地理解到它。比如說她們對藏傳佛教是怎麼想呢,我不覺得這是我解釋得到的問題。而且我喜歡她們是因為,我是用一種讚美的眼光去看著她,所以遠遠的看著她們在風雪中在聽經,她們走到山坡上閉關,很多時候保持一種距離,我覺得就已經很美好。我不想知道…當我把遠遠的鏡頭推到她們臉上的時候,她們在雪地裡很認真的,天氣很冷,她們很虔誠地看著上師、堪布,我覺得我的心裡只能說「她們跟我不一樣,她們走在一條我不太熟悉的道路上,她們的精神世界也是我從來沒有進去過」。但我覺得,我們知道之後,可以告訴觀眾的只有這麼多。因為這肯定不是一部弘揚佛法的紀錄片。
陳:金導演,你在這部影片當中不僅擔任導演,也兼任攝影及剪接,而在片尾字幕中,也看到你也有一個蠻大的團隊,有攝影助理,還有翻譯、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參與其中。請導演跟我們談一下你在拍攝這部影片的過程當中的一個團隊,比如說,就是有沒有找當地人幫忙,還是帶自己的團隊進去拍攝呢?
金:因為覺姆和寺廟裡的人大部分都不會聽漢語,我們漢族人過去是沒法交流的。那麼我們就需要一部分人是藏族人。有的,每一次(拍攝)都會有一部分是藏族人,他們擔任翻譯、協調、聯絡的工作,因為他們的體力較好,所以要協助搬運設備。而我們是從杭州過去,我們的工作室也會帶人去。在更多的時候,因為我們的製作組是臨時調度的,我們在出發前就會給很多人打電話,問他們去不去,有些人可能不怎麼認識,當然有些人就去了一次吧,所以人就有很多。對我們團隊來說,當我哪怕拍到80歲時,我們開玩笑說,這部片子好像是我們最苦的一個 ,可能是吧。因為它有各種的苦,就是說高原反應、寒冷、然後會生病,然後無法溝通,包括片子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處,又會出現種種的溝通和管控的問題,也會出現了這部片子到底85分鐘,用這樣的方式能不能成立起來,對我來說也不是百分百的確定,所以各種壓力就會很多吧。
陳:我們在這部電影裡看到非常非常震撼的雪景。請問你去拍攝的時候,其實都是剛好挑了在冬天的時候去拍攝,還是說你也有在其他季節的時候,到當地拍攝呢?
金:其實從我們的工作室來說,還真的沒那麼從容。有時候,我覺得有空就去,真的是這樣。有時候,我們就趕上他們的(藏族)節日過去,比如說你們看到有很多覺姆在跳舞,她們在夏天的時候跳舞。其實在很多人的印象裡,好像藏區的雪很多。但事實上的情況是這個地方的雪不算特別多。有時候,我們在冬天去20天都沒有雪。但是從我這個要求來說,我希望它有雪,還是需要等待。有時候,10月份下了雪,11、12月都不會下雪。但我希望它全片的雪花多一點,所以就需要等待,比如說我們有時候希望等雪,希望等暴雨,有時候希望各種吧……天氣吧。
陳: 剛剛導演說,這一部可能是你在創作當中遇到最多困難的電影。你在拍攝的過程裡,有沒有想說到哪一個節點,然後才是這部電影拍攝的一個終點?
金: 當初如果她們(覺姆)不走的話,我們也沒有想好怎樣結尾,或許也會想個辦法吧。其實她們陸陸續續地走,也走得很慢,直到2019年的時候才大批地走。這個結尾能告訴我甚麼呢? 或者說我應該怎麼來結尾呢? 我當時是想,她們是一群非常集聚修行的人, 即便離開了這個地方,她們也可以回到各自的家鄉、在懸崖上、在山谷間、在城市上空的那些山上,她們都在修行,大概用這個方式來結尾吧。有些人可能放棄了,但覺得不錯的人都跟我反映把它變成了一個很零散的狀態,她們在各個地方修行。
我要說一下,很多人問我為甚麼要拍這部影片,我自己也思考了很久為甚麼。應該是說,我在思考一個世界,它是跟我們思索的履歷和世界是不一樣的。它沒有弱肉強食,或者說沒有成功學的、特別環保的一群人,就是足夠用我們的熱情去讚美他們的一群人。所以我就會把它拍成一個我想要的感覺,但是我們也深深知道,美好的東西它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是幻想出來的,所以最後還是沒有了。就是說我們要面對這個世界,或者說我們來到了這個世界所保持的一種心態吧。真的,它是不存在的。我們在這個世界裡,很多時候會令我們很失望,也很沮喪,而且會覺得這個世界就是這樣。所以它的毀滅也好,也符合了我的想像吧。
陳:請問現場觀眾要提出問題嗎?
觀眾1:導演你好,我想問的是在現場的時候,你面對的都是很陌生的環境,語言又不通,尤其是你不能理解他們在做甚麼的時候,就單純是靠眼睛去觀察來決定拍攝的嗎?
金:對,就是說我要每天都要問自己我喜歡他們甚麼,我是被甚麼所感染的,雖然我也不懂得他們信仰的是甚麼佛。真的,有人告訴我是寧瑪派…但是我能看到這些人,他跟我們到底一樣不一樣,他離我們那麼遠,而且很多人是一輩子在這個白雪皚皚的地方,她們到底是為甚麼,我不知道,但是我能夠從遠遠的觀察、靜靜的觀察,能夠感受到一些「雖然我不了解你,但是我特別喜歡你」的這種感覺吧。我覺得這應該是美好的經歷,把她們曾經在一個美好的世界當中。
你看那些老奶奶(覺姆)年紀特別大,但是有些我們沒有剪進去嘛,在風雪裡面,零下二三十度的時候,她們也在聊一些關於宇宙的問題,很「靚」(美麗),因為現場是沒有人翻譯,因為我們不能翻譯,會影響到她們。但是回來以後,看到翻譯是她們在講宇宙和人類的關係。很多時候,她都在講一些我們可能叫做是…「生」與「 義」。很多時候,她們講的那些話也打開了我的一點好奇,甚至是哲學意味的東西,我覺得令我感到很好奇,她們為何會在討論如此深奧的,一些關於基礎、生命啟蒙和一些非常哲思的東西呢?所以我覺得這些師父(覺姆)是值得去仰望她,我們只是不理解她而已。
觀眾2:導演你好,非常感謝你帶來了一部非常好的試片。我有一個好奇的地方就是你學拍電影、拍紀錄片的初心是怎樣的? 然後到了這部影片的時候,中間有沒有甚麼變化去拍攝這部影片呢?
金:原來的時候,可能我們原來拍攝的時候就希望自己的影像被更多人看到。但是我後來發現不是這樣的,比如說包括她們的修行、那個宗教,我也相信不是被很多人所接受,是吧? 那麼我們的影像也是如此。所以說,我們的影像這麼緩慢,然後師父(上師)又在講一些非常兇險的故事,所以很多人都堅持不下去。但是作為一個導演,我們要明白的是,這樣的影片或許它是有意義的,有一些人類學和哲學上的意義,或者更多意義,或多或少吧。但是我們拍它是為了甚麼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或許是為了在幾十年後,當有人要去研究、去關注這些人的時候,他也可以有一些印象的繼承吧,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他們可供研究的信息,或者說藏人在那個時候經歷了甚麼, 或許能發現一些蛛絲螞跡吧。……我可以用一個遠遠的距離,保持距離,可以去讚美她,就是我憑我的直覺,我覺得這群人並不是一般的人,我覺得她們是在做一些可能是了不起的事情,或者說值得紀錄、去反觀我們的生活,師父(上師)不像她們那麼超脫、或者不像她們那麼純粹,有一些思考。
觀眾3:我想向導演提出兩個問題。請問你的工作人員住在哪裡? 他們是否住在小木屋內?
金:工作人員住在寺廟外面,離她們很近。我們出來的地方如果出來到她們居住的地方大概是5分鐘,可能更快,有時候1至3分鐘,因為我們住得很近,我們都是住在很簡陋的招待所, 我們住一晚,一張床最便宜的是15元、20元,後來是30元。
觀眾3:第二,請問你等待下雪 、等待下大雨、請問是不是因為現場環境能幫助你呈現你想拍攝的對象的心路歷程呢?
金:我們拍攝這些景象的時候,其實我們在拍天葬也好,拍攝在室外聽經,但是我需要這些場景去呈現,效果會更好。比如說你們會看到有些畫面,天曚曚亮還沒有亮的時候,地上全是雪,然後她們很多人走在那些路途看不見的地方,包括在天葬的時候,有很多雪落下了,我們也在追求那些時刻吧,希望能呈現自然現象跟她們融為一體的感覺。
因為我們認為那些風聲、那些雨、那些雪,在我的眼中都是個元素,它們都是代表一種貞烈的元素,是來自於自然的。對,我特別希望它存在,所以我全片沒有用音樂,我希望一切都是來自於自然界的。
觀眾4:導演你好,我想請問你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是第一次看跟藏族或藏區相關的一些紀錄片。那麼我第一次看的話,其實也有感覺到非常多震撼的地方,包括剛才多次聽到你說的「我們跟他們並不一樣」,但是在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一樣的地方。比如說小孩在考試的時候,她多少也會有些緊張;或是有人在聽經的時候,好像是在開小差,就是這些場景。我想問一下你在拍攝過程裡,給你最大的震撼是甚麼?
金: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最震撼的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們的時候。因為我之前也去過很多藏區,但是當我2014年冬天時遇見她們的時候,我當時真的發現了一個我從來不熟悉的一個「王國」。其實如果在未來的拍攝當中,能遇到這樣的地方,我肯定也會拍攝,就是我從來沒有見過,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地方,看到跟我們如此不同,所有東西都不一樣?我可能也會拍,也不管別人說你是不是在練習,我也願意用我的時間盡量去紀錄她們。因為你會發現幾千個人,穿著一樣,甚至是上萬人都穿著絳紅色的僧袍,在雪面上走過去的那一刻,你會發現好像真的絕對要去紀錄她們的感覺。最震撼的是2014年的冬天,就覺得那群人真的需要我們去紀錄它。而且我當時的感覺是它很快就要被消失了,因為無論是商業還是甚麼的力量,它肯定會消失。因為那個寺廟的女性最多的時候我聽說有2至3萬人,我去拍攝的時候應該有1至2萬人。現在的話也有,現在我聽說有3000人吧。但是很多都不一樣了,因為它要說讓很多覺姆要回到自己的家鄉,比如說各個地方,西藏、青海等,(來自)各個地方的都回去,只留下本地人。但有人跟我說,很多離開的覺姆都很優秀,打比方就是多數都是非常刻苦和認真,都回去了。所以,現在如果去看她們的話,大家應該不會有甚麼震撼了吧,就相當於色達…..
從外貌上來看的話,色達以前可能比亞青更要震撼,現在的話我覺得…若拍攝的話,從我的感覺來說,亞青可能會更加接近我想要的「人類民俗學」的感覺吧。
第二個問題是,剛才你有說到在要不要呈現那位男上師的鏡頭時,其實是一種選擇吧,算是攝製組的一個選擇。然後,這個鏡頭讓我們感覺到男上師的畫外音就像讓觀眾覺得他是一個可能是「上帝之音」之類,就是對於那些修行人來說,男上師說的話說得直白一點,就像聖旨一樣。這樣好像是一個創作的選擇。所以,(你)覺得作為一個紀錄片創作者,紀錄與創作之間到底是怎樣達到平衡呢?
第二個就是你說到的,就是當我如果說不拍攝那個男上師的時候,或許會給別人有這樣的感覺是,上師在那個地方確實是有一種這樣的威嚴在的,即是權威…對,沒錯。
陳:觀眾剛才提到,你在紀錄跟創作之間的平衡,也請你回應一下。
金:因為我不是特別明白剛才問題的涵意…我顧及的意思就是說,導演認為一個導演紀錄了這樣的地方的時候,他拍出來肯定是有各不相同吧。所以說,我的片子給國內很多導演看過,我就會發現這個導演如果擅長於美學、詩意的話,他就會喜歡。若是喜歡記事、講故事的導演,他就不喜歡,他覺得你這部片子沒有意義,希望你能夠了解覺姆的前世今生,她修了甚麼法,她為甚麼要來,她回家之後經歷了甚麼等等。你們也許想過吧,她們回家後,父母是怎麼對待她呢?但是,這些是另外一部紀錄片了吧。
觀眾5:你好導演,是的,很感謝你拍攝了這部影片,去紀錄了一群生活方式不一樣的人,這是很震撼的。我想問的是因為覺姆要撤退…可能根據我比較淺的認識,就是可能政府會對一些少數民族可能有一些干預,或者可能是迫害,在影片的後半段看到的是,就是亞青寺,政府好像趕走了那裡的僧侶,可是感覺就是有一大部分的人,即是在影片的前半段就是看見那些藏人也可以有他們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文化和宗教,都是有一定的空間可以存在的。然後感覺就是整部影片裡面,政府或者體制的角色就是比較隱晦,可能會有一點點就是,那個上師說「不要停止修行,除非政府來停止」 這樣,或者可能有一些政治宣傳這樣,所以我想問的就是在藏區裡,政府其實對於那些藏人的生活方式的干預有多大呢,或者說可能導演想要隱晦地去表達這一種…就是刻意隱晦地表達這種干預嗎?
金:我們在片子一開始的時候,是沒有從這個方向拍的,更何況在那個時候,一開始的時候,我們也沒有聽到,或者說我們不知道這些事情的發生,就是有沒有覺姆走掉,我們是不知道的。因為前幾年的時候,一開始人那麼多,所以我們拍了幾年之後,到最後一年才發生這樣的事情。等到最後一年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想拍也拍不下去了,所以也只能結束,這是第一點。
然後你們說到的這個事情,就是說…我們這部影片大概從風格上來說,這樣前面的50、60分鐘是如此平穩, 我們好像從創作角度都不是和在結尾出現了一個非常令我們覺得在節奏或者氣氛的這種…影像風格上產生大的變化。好像我不是特別能夠適應,或者說我沒有把握能這樣做,這是第二點。……
但另外一個是,其實有沒有發生過,或者有發生過, 其實我們也拍不到,真的拍不到。它是不可能會被我們拍到的,完全不可能,不可以。尤其是我不知道別的地方,反正我拍的那個地方是。是的,我肯定拍不到,我無論如何想拍,想盡任何一個辦法都不可能,反正做不到這一點。後來我們就會說,我們這部影片到底在反映甚麼。所以有一個我的朋友、我的監製也跟我說,其實這次讓她們回家對她們這些修行人來說,或者對於一個人來說,並不是一個最大的苦難。對於一個修行人來說。因為她的內心當中,她會看得更加遠,一個人生的苦難,(她)看到的是世界的苦難。所以說,這些就是給她上了一堂生動的課吧,她只是換了一個地方繼續修行。所以影片的結尾應該是這樣的一種結尾方式。
陳:我想順著這個問題再追問。因為像這部電影的話,其實到了後半段的時候,當中也有一些蠻震撼的。比如說我們也會聽到有一位覺姆說,其實她已經預備要為她自己的信仰犧牲,然後是因為她的老師勸她要珍惜生命,也要回到家鄉。其實你在當地的觀察,這些覺姆對於信仰有一種堅決的投入,導演你在現場觀察的時候是怎樣的? 因為可以看到(影片)最後,也可看到拍攝她們回家的一些片段和過程。
金:我們當時應該是在2018、2019年就進不去了,這兩年就進不去了。你們所看到的影片當中只是一點點,就像一條頭髮絲般的量,沒有的,其實沒有看到那個不太感覺…就是一個象徵性的「來像」,好像飛上飛機,兩三下就走了。那個不是的。真正的現實,我也有見到過。所以,或許我們是把一場非常大的一個痛苦,把它延長起來,讓觀眾去想,但我們後來在她們的老家,都遇到她們,她們都回去了。她們在那個時候對我很信任,也像是見到一個朋友一樣,她們告訴我,當時我們在亞青寺的時候,因為她們的管理很嚴格,所以她不好意思跟我們打招呼。現在,我們來到她的老家,跟她們特別好關係,但她們的條件也非常艱苦,因此我們一個一個地方去找她們在哪裡。所以,有時候找到100多人,有時候只找到5個人,6個人也有。然後大家也沒有說甚麼關於那件事情,有些人已經不會聊了,不想再聊。有些人會思鄉,會聊一些。那我只能夠象徵性地說一點點吧,只能從她們的片言隻語中,似乎隱約地展現了一點心裡面的想法,好像曾經發生了甚麼。
陳:她們的老家也是在四川,還是在其他地方?
金:有很多地方。有些在四川的各個縣市,例如白玉縣、甘孜縣、有些人在理塘、爐霍縣、道孚縣等地。還有些是在西藏和青海各地、有些是在甘肅南部、有些則在雲南,雲南比較少吧。所以人就有很多。
陳:她們除了被逼回家,後來又加上疫情,請問你現在還有沒有知道她們的近況,或是亞青寺現在的狀況呢?
金:三年疫情的管控,其實大家現在也不太知道了。我們只是看到有些藏族人去那邊就問一下,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大家都進不去了,因為疫情防控進不去,現在已經拒絕遊客,不知道以後會怎樣,有人說它可能永久都不開放了。
那些回到老家的人很艱辛的,因為其實她們回不到家裡去了。然而她們要修行,但在她們的老家,很多寺廟都不想接納她們,所以就要想辦法找一個地方,例如5個人、10個人這樣,大家找各種地方去繼續修行。因此那個康布不是說了一句話嗎,他說:「你們在寺廟的時候,大家就是築在一起的鋼鐵;你們離開之後,就像道路、攀流從水流出的養分。」他這個比喻講得特別形象。
觀眾6:你好導演,我記得在片段裡面有一段讓我覺得很好奇,就是有些覺姆去世了,然後她們(的遺體)處理的方式是讓那些鳥來吃掉她們,我想知道你當時的拍攝過程是怎樣的?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誤。
(註:天葬儀式裡,死者的遺體會被天葬師處理,割成塊狀,然後讓禿鷹啃食。)
金:因為我覺得很多覺姆是在亞青寺走向死亡,所以雖然我覺得很殘酷,要去拍攝她們,但是也有必要向觀眾交代這個過程。因此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等了很久,等到夏天、等到暴雨,等到了她躺在天葬台上。對了,很多人也有爭議說為甚麼要展示這個畫面,但我認為或許有人會覺得這一課並不是那麼殘忍。對,我希望有人能夠明白她的一生;她在死亡時給禿鷹吃掉,對她是一種榮譽。所以我們盡量是遠遠的。天葬師跟我們挺好,都給我們拍攝,我都可以拍攝到,所以我們都是盡量遠遠地拍攝,沒有太近,但我還是想展示這一個片段給觀眾,在冬天、在夏天。所以,雨和雪好像是一場儀式,我的感覺是這樣。在暴雨如注當中離開,或者是讓儀式感更強一些,更美好一點的感覺,是在我的心中。
陳:今天非常感謝金導演願意跟我們分享創作的心路歷程,謝謝。
簡介:
金華青曾執導《呼嘯的金屬》、《花朵》、《奔跑的黃昏》等影片,獲得第9屆墨西哥城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最佳電視紀錄片、第33屆德黑蘭國際短片電影節最佳影片、2008年廣州國際紀錄片大會評委獎等五十多項國際獎;新作《絳紅森林》迄今獲第41屆美國夏威夷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第25屆捷克伊赫拉瓦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特別提及獎等4個影展獎項,入圍2022年愛爾蘭都柏林國際電影節、希臘塞薩洛尼基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等。他有5次影展評審經歷,包括擔任第21屆法國沃蘇勒亞洲國際電影節NETPAC獎評委、第33屆黑山新海爾采格國際電影節紀錄片擔任評委;擔任浙江傳媒學院文化創意學院等中國12所高校創作導師。
與談人陳智廷是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研究助理教授,香港粵語片研究會及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員。他在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香港大學音樂學博士,並專攻華語電影、亞洲電影、電影音樂與聲音研究。他曾任香港鮮浪潮國際短片節評審、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初選小組委員、山一女導演短片扶植計畫初選導師、香港同志影展短片大獎評審、ifva亞洲新力量組初選評審。現正研究華語歌舞片,六十年代香港實驗電影與何藩影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