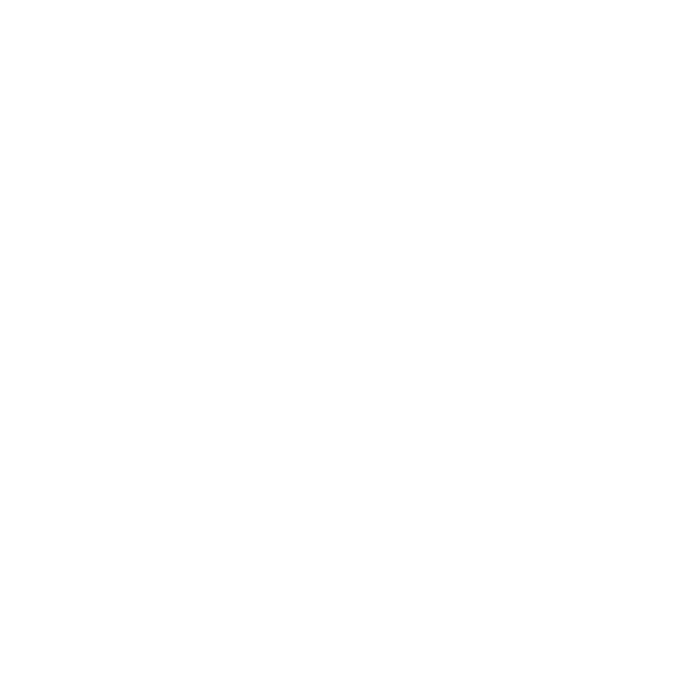4月11日的晚上,我們很高興可以與香港大學眾多部門合作,把《塑料王國》再次帶到香港觀眾跟前,並邀得呂秉權先生為為主持,與影片導演王久良先生及嘉賓朱漢強先生大談環保。
主持﹕呂秉權
嘉賓﹕王久良導演、朱漢強先生 (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

呂﹕我們丟垃圾,垃圾就遠離我們 ; 他們丟垃圾,這個垃圾好像跟他們長期在一起。垃圾跟我們的生活,還有世界的垃圾跟中國的這個問題交纏在一起。我們的行為、決定、生活的方式影響到小孩的一生。那我想先問王導演一開始是怎麼跟垃圾這課題結緣的呢?
王﹕首先想感謝到場的每一位朋友,你們的到來是對我很大的支持。我想沒有人喜歡垃圾,或者說,當你拍照片也不會喜歡拍垃圾照片。我拍《垃圾圍城》之前,拍的都是非常美的照片,可是在我尋找那些非常美的照片的過程中,我發現了很多不美好的地方,特別是我的家鄉。可能別的地方被污染時,你不會有太大的感想,但當一個人的家鄉產生了不好的變化時,感受到的震動及影響是非常之大。所以從2008年起,我關注垃圾的問題。也想透過垃圾場,去看背後消費主義的運作。
呂﹕你一開始去做垃圾這個課題時,可以說是用一個挺山寨的方式,非常原始地去跟蹤。《垃圾圍城》是拍了北京四百多個垃圾場,走了一萬三千公里的距離,這個等於是從北京到上海走十遍的距離,可以分享一下這個距離是怎麼弄出來的?
王﹕當時決定去拍垃圾場的時候,有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問題冒出來﹕垃圾場在哪?我那時在北京已經生活了五年,但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所以當我開始做的時候,我忽然發現我不知道垃圾場在哪裡。通過媒體、通過網絡,各種渠道去搜索,信息真的很少,所以我就用很原始的方法,每天清晨起床跟著我家的垃圾整個的流向,最終去到距離我家只有六、七公里的垃圾場。所以不管是怎樣的問題,只要想辦法就會有辦法。

呂﹕然後你做《垃圾圍城》時,什麼情景帶來了最大的震撼?
王﹕我想不到垃圾離我們這麼近,因為在我尋找垃圾場的時候,發現它們就在我們身邊。第二,它給我們的環境及自身帶來的影響是難以想像的。在一個垃圾場,我看見羊在食垃圾,然後就產生了一個不好的聯想。羊在食垃圾,我在食羊肉,相當於我在食垃圾了。垃圾的影響最終還是會回到我們身上,好像你焚燒垃圾,污染物流到河流,受害的還是我們。我做這影片時就覺得我對垃圾的認識實在太少了。
呂﹕你為這件事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因為基本上你每天都待在垃圾場,那給你的身上帶來了什麼痕跡?
王﹕其實還好。反而是我在拍《塑料王國》時就切身的受到一點小傷害,我的眉心有一個小傷痕,六年過去,現在已經平下來,但當時是一個非常大的膿包。後來我自己去查資料,去診所,才發現那是叫氯痤瘡,就是接觸氯元素過多的後果。我不是特別個案。在我整個的拍攝過程中,很多人的身體上都長了氯痤瘡。我覺得這是塑料對他們,還有對我自己產生的最真切的傷害。一個小疤,一個小膿瘡,都比不上整個塑料產業為他們帶來的癌症跟死亡。
呂﹕你拍完《垃圾圍城》這個比較龐大的計劃,再轉過來拍攝《塑料王國》的時候,思路上有否改變?因為《塑料王國》表面上只聚焦在兩個家庭,但是透過他們的故事是可以看見世界、看見大局,你是怎麼去深化這個思路,變成我們今天看到的影片?
王﹕簡單說一下,我一開始就特想知道,外國的垃圾到中國來是會怎麼處理,在處理的過程中,對環境產成了什麼影響,又對人造成了什麼傷害。但事實是,當我在調研、拍攝的過程中,發現垃圾問題或許只是一個載體,它背後透露的問題其實超出了垃圾、環境這些議題,我們可以從影片裡可以看到現在中國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兒童教育、貧富分化,以及背後的權力和資本主義的邏輯。
呂﹕對,我想影片中的家庭就是我們很熟悉的低端人口吧。當中的小孩通過垃圾去認識世界、去學英語,垃圾變成小孩子的玩具,然後回收場的老闆通過垃圾致富。我們知道你長期在那個環境拍攝,身歷其境,有很多情況是我們想像不到的,那當時有什麼是我們看不到但你感受到的東西?

王﹕我覺得電影裡呈現了很多,那個很糟糕的環境,那陣臭味,它對我們身體造成的傷害,但這些還不是最令人難過的。難過的是看見我們的下一代,這麼多的孩子在那種環境裡。包括電影的最後一幕,那些小孩在著火的垃圾場。
像你開場所言,我們大人從國外進垃圾,但切身收到傷害的是我們的孩子。所以我會想,我們大人為小孩的未來帶來了什麼,真正去解決問題,試圖去滅火的恰恰是小孩,所以我在整個拍攝過程,我最關心的是那些孩子。
呂﹕王導演也是一名爸爸,有一個八歲的小孩。相信為人父母,看到小孩在垃圾堆中打滾時都特別難受,最後一幕他們在滅火,不知道最終他們有否滅火成功。但中國在去年底開始停收外國進口的垃圾,相信這或多或少也跟王導演的這部片子有一定的關係,這方面我想就請教朱先生,其實自《塑料王國》面世以來,現在中國內地上的一些政策發展的情況是怎樣?
朱﹕我想先分享一點我的感受,這個紀錄片最後一句話是﹕那邊還在燒!小孩在這邊做滅火的事情,大人的東西在那邊還在燒。這個影片對我衝擊很大,我的小孩,大概就是依姐的年齡,還有久良跟秉權的孩子也是差不多大,作為爸爸看見小孩子在垃圾堆中翻滾是很難受的,所以今天拉了小孩來看。
講新的狀況之前,我這樣說吧,我以前是做記者的,在95, 96年的時候,中國有嘗試修改一些法令,讓一些外國的洋垃圾不能進口,在96年七月的時候有一艘去福建、一艘去上海的船,幾百公噸的船進不去,來了香港,而那些所謂的回收品,其實裡頭有很多是不能回收的垃圾,但那時大家並沒有什麼大的反應,只當是一單普通的新聞。我想說的是,內地的那個「塑料王國」,香港絕對有份造成的,不光是說我們所收集然後出口的廢物。而是香港作為一個所謂的自由港,在把有問題的廢物輸到內地的數量上,絕對是排行前三。有一個數字大家可能不知道,在中國收窄了廢物進口以後,一間顧問公司進行了一個調查,預計每年會有一百萬櫃的垃圾不能進到內地,一百萬櫃是怎麼樣的概念呢?就是等於中國每年貨櫃進口的百份之七。這個數字從來沒有在媒體上報過,而當中有兩成至三成是經香港到達內地。那現在至少有一百萬櫃會不見了,這是一個比較概括的狀況。
呂﹕聽到這個多的數字,壓迫感很大。但對我們很多人來說,我們把垃圾丟出去,不像他們一樣需要住在垃圾堆中。你有什麼呼籲可以讓大家作出一些行為上的改變,讓他們意識到垃圾就在我們身邊,我們在毒害身邊的人。
朱﹕我想有兩點,因為我們生活在城市當中,所以就沒有這樣的意識,覺得垃圾看不見就好了。大家還比較有公德心,會把垃圾丟到垃圾桶或回收箱,好像這就已經完成了我們的公民責任。不過很多時候,丟在裡面的垃圾只是從垃圾桶轉移到垃圾場。我們的堆填區本來預計是可以用15到25年,三個堆填區在94-96年全數落成,到2001年時香港政府就已經說如果根據現時丟垃圾的速度的話,3個堆填區很快就會滿了。我們那時才用幾年而已。這就是導演所說的,消費主義在香港的狀況。我們沒有反省的話,只是不斷擴建堆填區及焚化爐,那是一個方法,但絕對不是一個聰明的方法。
呂﹕我想導演你拍完這部片子以後,一定有很深的內省跟感受。想知道從你個人到你生活的社區,你觀察到什麼變化嗎?然後對這種改變有什麼感受?
王﹕我首先補充一下關於我們能做什麼的問題。我常思想個人需求跟環保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我覺得我們一方面要加強自己的環保意識,盡可能少作不必要的消費 ; 另一方面去倡導生產者,向他們施予壓力,反映我們的訴求。
至於轉變的問題,我作為一個電影人,我覺得我的角色應該是提問題,當然我也會盡所能的去參與問題的解決。但重要的先提出問題,把問題放在枱面上,引起初步的關注,才有解決的可能。所以我們的電影應該是有這個作用。我不敢說這部電影在影響國家的政策上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我知道背後的努力是有價值的。所以中國政府去年七月頒佈了法令從2018年1月1日起限制二十四種洋垃圾的進口,雖然是較武斷的命令,但至少是斬釘截鐵地在解決洋垃圾進口帶來的破壞。
不要再跟我說那靠洋垃圾維生的人怎麼辦。資本的流動性是你想像不到的,它總會流到應該去的地方。即便人不幹這些對環境造成重大傷害的產業也能生活得好好。

朱﹕想知道電影裡那個垃圾場的場主跟依姐後來怎麼樣了?
王﹕電影不僅是改變電影的作者,還有電影周圍的人。有人跟我說,紀錄片的導演應該保持中立,用客觀的態度去看待被拍的人,我說這個是個偽命題,這是假的。但你跟那些人一起時,你的情緒會跟隨他們一起受到牽動,所以不可能不介入他們的生活,當你看到小女孩的家庭一年一年的努力,只是為了賺點錢回家去蓋個房子,以及讓小女孩去上學時。但三年過去了,你發現小女孩這小小的願望,靠著這產業並不足以給予。這個如此龐大的產業,卻連這一個小女孩的命也不能改變。三年過去了,那個時候我想我惟一能做就是放下攝影機。我跟我的制片方CNEX拿出了一點錢幫這家人回到家鄉。在2014年8月時,依姐的弟弟都去上學了。我們2014年春天拍畢不久後,王坤也關閉了工場,我想當中是有受我的影響的。在我沒有拍攝的期間,我會坐下來跟他分享我搜集的信息,分析這個產業的利弊、未來的發展是否能讓他過上更好的生治。那半年之後他就把工場關了,變了卡車司機,反正他也喜歡車。
呂﹕接下來我相信有很多觀眾也有問題想跟導演交流。
觀眾﹕我是來自台灣的,我從小就對我們做回收做得很好而自豪,但看完這部片以後,我覺得是對我信仰最大的諷刺,但也要謝謝你讓我們開眼界。我想問的是,你參與過這麼多的分享,相信也聽很多不同的問題,有沒有一些方向是觀眾也沒有提過,但你是很想分享的?謝謝。
王﹕對,很多問題我已經回答很多遍了,但是我每次也會努力的詳細回答。我覺得要對觀眾的理解能力有信心,你在電影埋了多少,觀眾都能看得到,甚至於一個鏡頭,一個聲音。所以說有什麼沒有問過的我倒真想不起,家庭、教育,孩子,甚至於女權也問到了。我第一次聽到關於女權的問題是在紐約的MOMA放映時,有一個女性就說她很想知道依姐的媽媽跟王坤的妻子是怎樣的。但我沒有看到他們的話語權,你作為一個男性導演,這樣的安排是刻意為之的嗎?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那我現在自己提起來,我就自己回答吧。
第一是因為這兩個家庭確實仍是男性主導。第二依姐的媽媽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人,真的非常善良,我特別想知道她對自己的家庭從事這個產業有什麼想法。但因為她是彝族人,又不懂說漢語,我們就溝通不了。坤的妻子也是一個很好的人,而且是很真誠的跟我談這個產業的弊端的人,她很坦白地說她並不想幹這個,因為她明白當中的害處。我是真的很欣賞這些女性既溫柔又強大的聲音。
觀眾﹕王導演你好,我現在是在讀港大醫學院的博士生,我很久之前就對你的這部紀錄片非常關注,它對我的震撼非常大,因為它跟我的研究相關的。我特別關心片中小孩子的健康狀況,想知道你在這方面有沒有繼續跟進?還有國家的衛生部門有沒有相應的措施保護他們?
王﹕謝謝你的提問。這也是關於每個人能做什麼的問題,我是電影人,我就去拍電影 ; 你是醫學博士,你就用你的專門所長去為這個社會做一些事。我覺得只要把你現在在做的事情做好就足夠了。我去拍塑料,我對塑料的所有知識就是恰恰是來自科學家的研究 ; 我想知道國家的貿易情況,來源恰恰就是來自專門研究這方面的人。我毫不矯情的說,我們都是一起在做這件事的。
觀眾﹕我的問題是關於其他經營或在回收場工作的其他家庭。因為剛才有提到,內地收緊了洋垃圾的進口,那這個政策是不是導致了很多回收場的關閉,實際的情況是怎樣的?另外就是環保教育是很重要,那國內,尤其是關於塑膠的環保教育又是怎樣的?
王﹕簡單說幾句,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很突然的政策頒佈,但對這個產業的從業者來說是不突然的。在2014年底,「塑料王國」的媒體版公佈了,然後在2015跟2016年這兩年間,整個產業內部其實有很大的波動。即便是這項有關洋垃圾進口的政策,也是從2017年3月就開始決定政策,到真正停止進口其實是2018年1月1日,這中間是有個過程的。這個過程或許不足以讓一些工場作出調整,但我相信還是有一定的空間的。而且我個人非常贊同這種斬立決的方式,長痛不如短痛,也會讓外國了解到他們以往透過中國解決自己垃圾的模式是有問題的,要感受到痛,他們才會改變。這是很大的議題,我只能簡單的說。
關於塑料的教育,我只能說是真的很不夠。或許可以由朱先生在這方面補充。

朱﹕這個問題實在太重要。久良的話我大部分同意,一刀切是有必要的,但要怎樣切才能更好地接軌,這方面可能政府就沒想得那麼細。但重要的是這個命令要持續的做,不能做三、四個月就停。大家常常說,歐洲國家的回收做得不錯,但做得不錯的很多時只是回收方面,那處理呢?處理的部分就交給中國,這二十年來,都是習慣了這個模式。香港也是一樣呀,打包就出口了。所以說這個條例頒佈後,最能感受到痛的是我們香港。好像2013年內地的陸籬行動,那次官方數字是說有200多櫃的垃圾留在香港,實際的數字是5000到10000多櫃。
有一個問題我想全世界都在面對,但在大陸更甚,就是很多民間的環保團體努力在做,但教育的速度往往比不上破壞環境的速度。所以當再有人說,教育很重要,可以。但教育不是讓大家現在什麼都不做的藉口,還有教育的速度能不能提升。不然,你想像一下,依姐長大後這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觀眾﹕我其實是第2次看這部片了,也是很感動。你剛才說你以前是拍美麗的東西,那我想說在這部片子裡,最美麗的東西可能就是那些孩子呀,因為他們在面對我們導致的這麼不美好的世界時,要面對失望,面對大人失信的承諾時,他們也有很好的自我照顧的能力,把這些變成他們的玩具。我就是好奇,依姐現在已長大了,她有機會看到製作完成的影片嗎?如果有看的話,她有什麼想法?
王﹕因為我在開始調研時,我的孩子一歲,到影片拍完後,我的孩子六歲。整個拍攝的過程正好就是我小孩長大的過程,所以當時移情的心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我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敏感。我在拍攝剛開始時真的是義憤填膺,我當時跟媒體說了一句話﹕除了小孩,這裡的所有人我都不饒恕。因為每個人都是共謀。
依姐真的是非常懂事、通情達理的孩子,但到現在她還沒有看過電影,不過有看過一些報道,因為可以上網,我們也有微信。可是這個影片在大陸可以播放的渠道很少,我們又離得很遠等等原因吧。